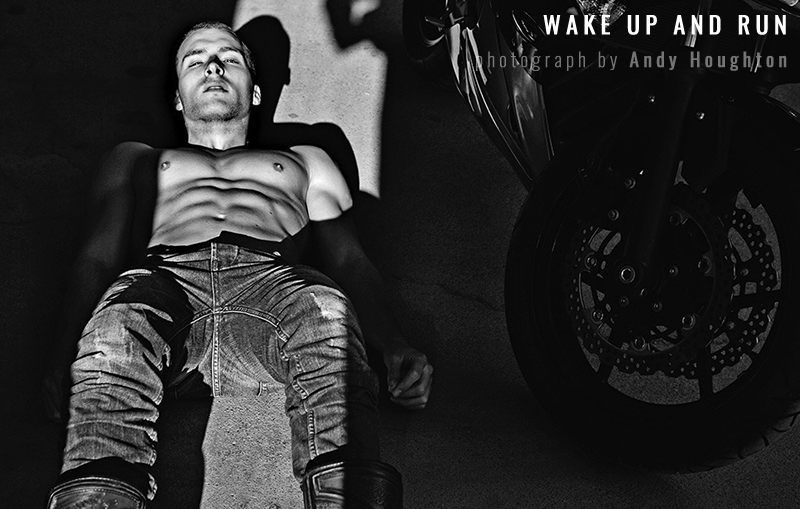情人节那天,兔兔除了得到KEVIN的主打礼物——一条ETRO的姜黄拼酒红斜纹超长围巾外,还意外的收到他老姐指定要他送的COMME DES GARCONS的ODEUA 53香水,以及棉棉的新书《PANDA SEX》。他个人认为送ETRO的围巾才比较有情人的味道,可是迫于他老姐的“淫威”,还是买了香水和书。突然就把他老姐崇拜得天昏地暗,居然明白川久保玲的无机香水、棉棉的文字跟兔兔这三个“存在”的内在关系——她她她```还真不是凡人的说.....那天KEVIN有幸重感冒,红着鼻子抱胖狐狸热水袋穿厚厚睡袍扮维尼熊,满屋子都被他生病的气味肥肥地填满,以至于兔子左手香水,右手拿书无耻地轻蔑他自选的情人节礼物时,都没敏感到一丝瘦瘦的愤怒努力挤进来急速膨胀直到爆发:“!!!!!!正式通知!现在我开始认真地生病去了!”咣当!哎,偶这个大宝贝BF终于发威了~~
呵呵,废话少说,本次沙龙的正题是,关注和讨论棉棉——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市中心”亚文化作家,这个“亚洲凶猛动物”。
棉棉的愤怒
by 发条兔兔
棉棉当然应该愤怒!
这个遭到主流文化生活场景中“正派体面”的大众指斥的“异端”,在以“残酷青春”为代价得到的惨痛经验,却被自我盟誓“我要赚钱,我会成为畅销书作者”的卫慧复制为符号化的“媚前卫”—这一通俗意义上的流行时尚以后,顺理成章地,主流媒体不容分说也把她划归在“以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行列。面对自己的作品以“性”与“隐私”的名义热销,棉棉愤怒地嘲笑自己的“出名是一件很狗屎的事!”
很可以理解她的愤怒,因为这也是兔兔的愤怒!
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一个代表,棉棉经历了噩梦般的“棉棉的故事”:十年的“动荡”岁月、三年的海洛因生涯、酗酒、车祸、自杀,以及无数失踪的朋友......这些“本质上可怕”的生活,带给棉棉的是“不可逆转”的代价。因为这生活,也因为这代价,使棉棉才有资格成为“黑暗处”的都市边缘人群的代言人,或谓精神偶像。
棉棉声称:“我的小说就是给活跃在这个城市中大大小小迪斯科舞厅里的问题青少年写的。”她很清醒,“大约有六成读过我的书的人实际上并不能读懂它,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理解。”于是她异常专注地为心目中生活状态在边缘地带的目标读者群写作。“我的残酷青春使我热爱所有被蹂躏的灵魂。”她确定。
然而,令人觉得嘲讽的是,在棉棉甫被文坛推出(《收获》上发表小说),到后来被炒作成为“七十年代后”的代表作家以及被强行冠上“美女作家”头衔的过程中,或许是出于吸引那“六成读者”的商业性考量,或许是出于安全发表的策略性考虑,或许只是策划者缺乏应有的判断力和精英素质,棉棉的“残酷青春祭”非但没有被有效的确认凸显,反而在大众对于“女作家大胆披露私人生活”的目光投注下,退为其次。引人注目的却是被粗鄙的无聊媒体争相炒作为“异端生活亲历者,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的表面生活方式。“性”和“隐私”从国内的传媒一直蔓延到国外的传媒和出版社,同一意义不厌其烦使用这一符号标签,甚至更为露骨,把棉棉的写作视为“这个新的,狂野中国最肮脏地下生活的见证人”,以此最大程度满足了最大多数窥阴癖的猎奇心态。
她怎么可能不愤怒!
有更多啼笑皆非的事情。
不少人买棉棉的书是因为喜欢卫慧,同样,更多的读者因为讨厌卫慧而拒斥棉棉,他们甚至都没有读过她和她的文字,单凭看某些无智商不负责的评论或者干脆想当然地就把她当作“卫慧的小姐妹”。(不过他们就是买了棉棉的书,也不会读懂。他们之中喜欢“伪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可以接受卫慧,但绝不会接受棉棉。在棉棉这里,他们得不到他们从主流文化场景当中想象出来的生活方式。她的前卫只会刺伤他们,拒绝了解的姿态只会让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他们可以理解可以模仿的生活。)
她跟她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得几乎是本质地区别。
棉棉这个“异端”,我们Queer的Queen,以“残酷青春”换来的故事和人物性格,在卫慧那个“宝贝”那里可笑地符号化,庸俗化后“时尚”登场。这些“本质上可怕地生活”带给棉棉的是“不可逆转”的代价和烁烁夺目地伤疤,而卫慧却在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克隆一个(群)人生命深处的痛,又残忍地剥离这种“痛”的深刻,异化成“另类”潇洒却失去内核的“酷”。从传播学的视点考量,卫慧的定位是一个居于相对“核心领域”的“畅销书作家”,她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赚钱。“我每天坐在电脑前面10个钟头的写作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为此,卫慧必须要以主流文化的大众为受众。于是她笔下所有的浪荡都无关乎淫欲,更无染于铜臭。每一次ML都由于对无望爱情的的固执追求,是奉向爱情祭坛的自戕。这一来,“爱情圣徒”绝世而独立,倾国倾城之余也暗自吻合了大众的传统审美伦理观。于是以“伪前卫”姿态出现的卫慧反而更有市场。
棉棉跟卫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她植根的土壤是被视为“噪音”的青少年亚文化(RESISTANCE干脆直接在他的研究中命其名为“抵抗的亚文化”)。卫慧是个在外面搞得实在乱了累了还是会回家喝了妈妈的粥睡觉的“宝贝”,主流文化有她容身的地方。可是棉棉不行,她是回不去的,她跟主导文化群体这个母体天然对立,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棉棉始终坚持自己的“个人化写作”,异常独立清醒地处于“边缘领域”,为“亚文化人群”代言。她是在街上长大的,她为她命运与共的群体代言是她自觉的责任,因此写作更具有某种“必要性”。当然,事实上棉棉的读者群既非有主流文化背景的大众人群,也不可能包括整个青少年亚文化群落的所有人群,真正理解并且深刻反思的也只是亚文化群落在文化上的代表者和诠释者,他们本身就是这一与主导文化群体相隔离的特殊文化语境的创造者。这个圈子由亚文化系统内,或与亚文化系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由艺术家、赞助者(譬如“爵士朗姆汽酒”)以及有物质基础支撑的自由艺术爱好者组成。在这个圈子内艺术家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用不着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受众已有足够的知识。受众成为创造者的支持群体,抵消了他们在一般公众眼里看到的对立。那么,他们的作品也只能在这个圈子得到认可,稍一越界,便会被肢解和歪曲.因此棉棉总是以鄙夷、厌恶、嘲讽的口吻谈及自己作品的流行:“看着我的盗版书和一些廉价的电子表一起被放在地摊上卖,我对自己说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流行的一天!”
边缘化生活让真正领受边缘化生活的人愤怒,伤痕累累,他们当然要向“意识形态领导权”挑战,不过,也许是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上了柔弱的印记,他们天生软弱,于是这种挑战不能象“反文化英雄”那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明确的反对形式,有详尽阐述的“可供选择的制度”。赫布迪奇认为,亚文化的挑战和抵抗是象征性的,主要透过特殊的消费习惯、透过生活方式暴露其“秘密”特性又传递它被禁忌的意义,指出“把次文化与更为正统的文化结构区分开来的,基本上是次文化的商品消费方式”。
说得很明白了。
在这个意义上,锐舞派对、酒吧、地下音乐、酒精、麻醉剂(我们的人不把它称为毒品)、性、某类风格的乐队、DJ、俱乐部文化、类型电影和唱片乃至特有的着装方式和作息时间,对于棉棉及其所属亚文化群体,包括兔兔在内而言,上述那些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都不是可能与公众分享的,那是我们自证互认的标识,是对“正常生活”极为认真的挑战。因为存在这样的“内因力”对抗,我们在世俗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或多或少地都会付出代价——兔兔的代价就是,被家庭和家庭所代表的那种社会文化背景所抛弃,被迫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离开了从小演习熟练的社交礼仪,离开了从四岁开始修习的舞蹈和舞台。要不是后来遇到KEVIN,兔兔也许到现在还会逡巡在那个城市著名的西区,黑暗的酒吧中,以寄生虫的美丽名义,待价而沽。
然而,我们对抗主流社会的文化场景,生活方式为什么会被主流社会的“媚前卫”者拷贝?这不得不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暗合了一般大众期待的某种新型的生活时尚。
应该看到,被模仿的只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各类子文化的代表。首先,在这个圈子创造作品的艺术家都不依靠自己的作品为生,(棉棉写作之外,更是一个被跨国公司艺术赞助的俱乐部文化经营者,她的CLUB CANDY在上海僳阳路1088号。)他们本身物质基础丰富,有能力享受主流社会中的大众所羡慕的生活(至于来源你就不用打听)。创作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钞票(事实上他们的作品由于本身的特质不可能有广大的受众群,不会有什么商业效应的,从而与“流行”无缘。),他们异常执著地坚持“个人化创作”,为自己所代表的文化群落代言或从“边缘化”生活中抽取艺术内涵,丰富和发展这种文化。
另一方面,被模仿的原因还因为“我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边缘化的自由艺术家绝大多数都具备高贵的家族传统和纯良的教养,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往往胜过大众式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从小就在品德,文化,礼仪上受过严苛的训练。造成了以后无论存身何处,都会显露出强烈的唯美气质。对比于没有良好的出身,却热衷于进出歌剧院、博物馆,在会员制的俱乐部斤斤计较苏格兰威士忌是纯麦芽的好,还是渗杂的好的那些广大“媚雅者”来说,显示了一种“种”上的优越。
似乎还应该提到“我们”特有的作息制度。随着泛政治化的收缩和市场经济的展开,“自由”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由”以及“自由”所表现出来的任何形式,只是在得到一份“稳定而体面”的职业后的梦想。他们要想保持“稳定而体面”,就不可能不遵循类似“朝九晚五”这样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自由”对他们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只是一个被传说中的“自由社会”允诺了的“个人生活空间”,因此,一旦有人在生活中或就是在其他表现载体上演习“下午四点起床,晚上组织主题派对,子夜后打开电脑......白天睡觉(除了乐队排练),晚上看书看书喝酒听音乐看电影弹琴唱歌。偶尔会去演出,偶尔会去外地旅行。”这样毫无压力的生活,他们怎么能不向往!
我们是异端,我们是Queer。我们真实地生活,生活真实地伤害我们。
我们不是愤青,我们没那样“辽阔”的视野和宽泛的人文胸怀。冷眼旁观,其实他们的愤怒大多乌托邦。可他们不论如何还是“自己人”,我们却是被隔离的“怪胎”。我们真的受了伤,伤口很真实,不小心触碰到依然鲜血淋漓,我们是被主导文化群体隔离的人群,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在自己的文化场景中生存,不会向谁要求强势话语权,了解也好,不了解也好,你在你的生活中生活,我在我的生活中生活。但如果谁要使我们的抵抗失去凭借,代价没有意义,我们当然可以愤怒,我们当然应该愤怒!
也因此,当我们的生活被“宝贝们”轻巧的复制成他们视为的“另类生活”的标志,以此“炫酷”,以此引导培育更多更年轻的“宝贝们”来肆意行而下地模仿,而后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时候,我们就会视为不仅仅是商业“盗版”那样的劫掠,而是面对面的挑衅,本质意义上的冒犯和亵渎!
棉棉的愤怒不是作秀,她的愤怒不但是她天然的权利,也是她天然的义务;
我们的愤怒不是无因的,因为生命中真实的伤口被偷窥,而后被恶心地拷贝成纹身在大街上流行!
当伤痕所具有的颠覆性被消解,时尚成大众文化中的波谱艺术符号,被侮辱的伤痕拥有者当然不会仍在边缘沉默——
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愤怒愤怒愤怒!
亨利·米勒在巴黎放浪形骸,凯鲁亚克永远颠簸在美国的公路上;
在亚洲,在今天的上海,有我们的棉棉傲世独立,激凸疏离的气质没有一丝媚态,也许只有ODEUA 53香水才可以作为她最好的注脚。
……
那一年,ROJAM DISCO里,看到她在兔兔头顶的DJ控制台上光彩四射,终于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