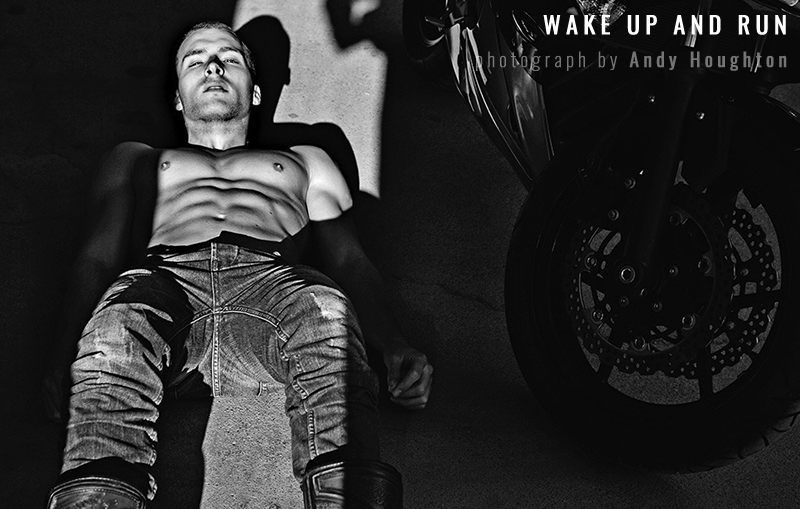向 日 葵 之 恋

对于这个男人,我该如何形容呢?疯狂已不再是他的标签,随着时光的祭奠,凡高的割耳更是成就了一段血性的爱情传说。当我们面对那些妖娆的鸢尾花与浓烈的向日葵时,扭曲的生长已经被画家赋予了真诚的吻。是的,当他要亲吻枪支时,却没有人来送别,哪怕他将成为后来二十世纪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偶像。同是画家的米勒点出了凡高的信仰,“艺术便是战斗。”所以在凡高心中,惟有艺术才是最考验人的忠诚——对生活的忠诚。或许,在别人看来(就连凡高本人也这样看),他其实是卑微的,除了精神的坚韧之外他完全没有更伟大的法宝,甚至可以说,凡高的偶像气质就正是建立在这最平民化最本源性的生活姿态。
《亲爱的提奥》是凡高那尤为著名的写给胞弟提奥的信件,他无意为自己立传,只是朴素率真地记录一段又一段在艺术饱满与生活贫困间挣扎的内心所感。当一个人有了倾谈对象之后,他的口吻是亲切且自然的,凡高有对自己亢奋的辩解与维护,但这种举措给予了提奥与我们这些读者别样的亲昵感。在生活中,无法解释那些不可抗力;但在艺术创作里,解释作品就是搭建封闭内心与外界的桥梁,凡高的执拗,正使得这过程充满宗教朝圣般的纯粹。于是,向日葵一朵一朵地绽放,在十四朵的时候,让瓶子插满了关于生活信念的花型书签。有一种雄心促使着他继续浇灌,直至花期已过,直至麦田枯黄乌鸦飞过,直至迷乱的星光在暗夜绕出无垠的旋涡。
“生命只不过是一种播种的季节,收获不在此地。”凡高愈来愈看明白的生活本质,竟在于脚底的土壤。有别于那些靠艺术盈利经商的人,他并不是苦于无法让作品卖钱,而是因作品在艺术交流圈里的缺席而愁苦。如果没有提奥,他没有能力去创作,这是物质条件;如果没有米勒等前辈,他没有精神去挖掘灵感,此为动力支撑。外力,既阻碍了凡高,也成就了他的炽烈风格。可是何等困境里,自我意志总是最牢靠的指路牌。你崇拜凡高,不就是因为这坚不可摧的斗志?然而你也知道,他的传奇,被夏天的花草树木唱尽了悲哀,最终由向日葵来代言,他对生活的忠诚不二。不是什么疯狂的色彩,不是构图的奇特或笔法的标新立异,凡高的伟大就在于对生活忠诚的爱。
一切创作,一切人类为解读自然而进行的创作,无不基于对生活本身的爱。正是这种爱,凝结了所谓的伟大。即便凡高用纱布遮着半边脸,用笔稚拙地画自我肖像,他所描绘的真性情男人已栩栩如生。可是,本书中的提奥弟弟怜爱地暗地指责,向日葵、鸢尾花、绿柏树们也同样指责凡高,他有一双孩童的眼睛。当然,在1890年凡高死后的这一百多年间,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的这双眼睛,以及眼眸幽深处的灵魂。
诗 人 的 词 条

他的身份是诗人。他想表达自我的看法,于是文字成了极富张力的陈述台。在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对面,是他故乡波兰的社会体制,无论多么陈腐,他也扼不住自身对故土的深情。所以在他这本看似琐碎的回忆录中,确实有着格外深沉而连贯的主题:对波兰、尤其是家乡维尔诺的追忆。那些对自我的审视,与其说是安抚因流离他乡而带来的缺憾,还不如说是站在少年岁月的路口细嚼这抚育带来的恩惠。家乡对每个人来说是起点也是终点。朝花夕拾,米沃什能做的只是梳理一下。
作为回忆录,米沃什借用了小说中词条的写法来搭框立架。所以,本书的看点竟然成了诗人到底提及了哪些人物,这多少让猎奇的读者和批评家有了切入点。可惜又有点悲哀的是,在2004年8月诗人离世后,才涌发了真正的“米沃什热潮”,人们才真正积极地关注这位快要被忽视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且不说瑞典文学院对米沃什的态度,也不提波兰本土对诗人的偏见,仅从这句话来认识他的内心吧:“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各种反光的纠合点(a tangle of reflexes),一个舞中喝醉的孩子。”
有时候,文明社会的容忍程度把底线划到孩子这一阶层,无论多么反叛的行径,只会当成青春期的年少轻狂。世俗批评与个体反抗持续在战斗,从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子到当今体制社会下的每一个浪子。暧昧的政治异见者,或是尖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仅代表米沃什一方面的态度。往往在自我扣问中明晓的那些事实,诚挚得让世人惊叹不已。那么,诗人留下的回忆,也只不过是为纷杂的言论画上休止符,他无意解释,解释即让此书成为伪本。
弱点与摇摆不定,成为诗人的感性。抛开那些政治话语,无视各种鄙夷,米沃什更想执著地抒发他的家乡之爱。像认识到时间的瞬时性那样,他把场景的碎片集合在一起,编为词典,一本让他人走进米沃什诗性世界的ABC手册。然后他消失了,如最刚烈的摇滚歌星一样了结全部的哀怨,毕竟,“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所以我们都服从这一条规律,即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
最终我们的感叹也来不及弥补我们所犯的盲目。而米沃什说这些仅是孩子在认知起步时的情绪冲动与依恋情结。
夏 天 已 绽 放

可以说孩童的视角最纯粹,也可以说孩童视角的窥探最为自然。于是画家们返璞归真,于是诗人都会缅怀曾有的孩童时光,米沃什选择映射孩童的恋母情怀,而同为诗人的吉·格飞则在虚构与现实间游离,记录一份少年情事。
这是多么迷人的故事一点也不重要。《欲望初绽的夏天》作为他的第一部小说,像一朵蔓过黑夜边界的花,把迷香一缕缕塞进黎明的嘴里。惊世骇俗?离经叛道?此类评判有何准确性?这朵妖花被一位美妇握紧,她诱惑着他;这朵仙花也握在一名少年手心,他胆怯但反复不休地向她暗示、表白和悔叹。从各自立场上看,她和他本无交集。
可仿佛是年龄差颠倒、角色却不变的《洛丽塔》。少年西蒙才十二岁,女子茉内特大他整整三十岁。这距离又有何关系?少年抚着瘦弱的身躯,把女子当成最温暖的花丛。她,是洛丽塔,是生命之光,是欲念之火。那些数据事实大可被忽略,毕竟在黑暗中你只看到实在的女性,以及自己体内的生长,然后,少年抵达更为沉郁的世界。
可是为什么?“太阳可以像个疯子般地在麦田里打滚,天空可以织出一片无缝的蓝,大地老鼓可以像新鼓般地回响:但是对我而言,主调是哀伤的。”在不完全青春期时刻,少年所体验的无法获取的爱,被夏天赋予了残酷性,甚至死亡意识也溜了进来。她促成他生长,却扼杀了他的绽放。其实身为迷宫制造者的她,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无能为力。于是,在迷惑不解中的“我”和在欲念裹缠中的“他”成了少年西蒙的两个分身,同时充当了小男子汉的意志觉醒。成长期,仍在吐绿。哪怕夏天刚绽放就被狂风暴雨所摧毁。
青春并不是过错的集合。你我都还在经历漫长的青春期,未厌倦前就已死去。少年说太寂寞地在生长,少年还说,“而我,一无所有。”
05/2006
Today in History
2008 • Vol.01 - Aud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