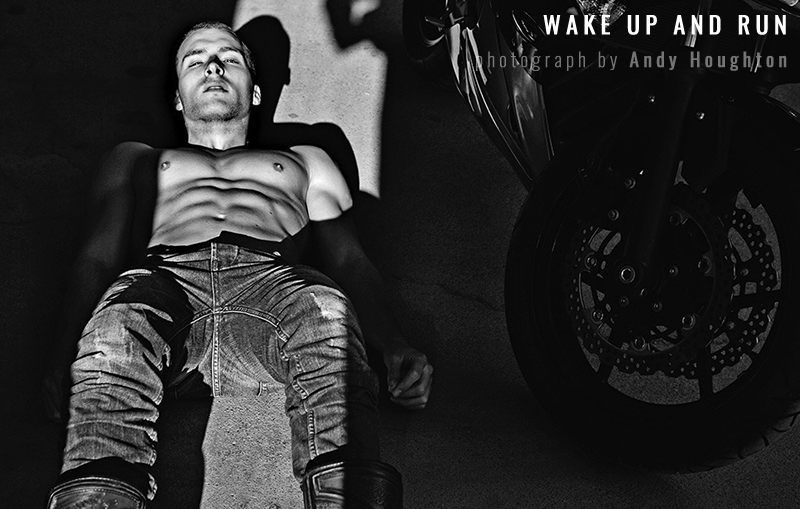吃
“你一直在想方设法把我给吃掉,不是吗?”她说。“你一直在想方设法同化我。不过我给你做了个替身,这东西你是会更喜欢的。你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吗?我给你拿把叉子来,”她又干巴巴地加上一句。
——第二部 · 30节
要是你爱的人给你来上这么一段,你能有多大勇气把那个“她”吃下去?这个可以吃的女人,她早已独具匠心地把爱情物化为一块人形松蛋糕。将这块爱情吃下去,将迷茫之心吞吃,埋葬。
所谓的理解与知心,在食欲面前无力。
你想控制她,想她归属你。但你真能吃下么?吃下整个她的精神、灵魂,于是才成立你绝对的爱。倾入,与付出,都以此来断定。
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完成这部处女作,沉寂了四年,终获出版后掀起了女权问题的波澜。她本人以为,与其说是女权主义,还不如说它是原女权主义的作品。以此而言,玛丽安便是阿特伍德对当时加拿大社会中孕育的女性本原归属的产儿。
玛丽安沉着安稳,是个有点疯狂的平常与非平常女人,和男友相处和谐。仅是表象。骨子里的迷茫不知所归时刻渗透着句句轻松诙谐的言语,字字浸染。传统优质男彼得外貌与内涵无以挑剔,却无法摆脱“结婚惧恐症”的心病。一群单身朋友的亲密相聚,骤然间一个个离他而去,奔上结婚的正道。
彼得每遭受一次离弃便郁闷一次,压抑到难以解脱。从内而出的困境迷陷了他。每次必找玛丽安做爱,怪异得纯属自我安慰。第一次,是在他卧室的羊皮上,第二次他开车开四个小时,在田野里一块粗毛毯上,第三次便在其卧室冷硬的浴缸里。
彼得行为中的大男子主义是千百年来的正统精神,延及社会中性的地位对应。所谓强权或占有,不过是主观意识之外的一种冲动,将生理欲望的满溢上升到对精神抚慰的冲动。彼得想要的,仅是玛丽安对他自我压力与渴求的中间调解,偏激的做爱癖成为其形而上的爆破点。
然而玛丽安在恋爱行进中的疯狂更为天真。当彼得与她的朋友伦聊到兴起,全然冷落她的时候。玛丽安先是独自躲起来流泪一番,后来在几个人回家的途中猛然一个人发疯似的大跑大逃,尔后被彼得他们截住,又返回伦的公寓喝酒,但当玛丽安意识到他们三人沉浸在各自的事情里,她出奇地躲在床底,这样却意外窄小地找到了自我。
玛丽安以为,“我开始把他们看成是在‘上面’,我自己是在地下,我给自己掘了个小窝,我觉得很安逸。”这绝不是孤单者的自嘲。
玛丽安莫名地退缩回孩子,躲匿在床底的世界,开始给自身与外部划上清晰界限。这一乖戾调皮的个性正是她想要的,就像她对同居女友恩斯特所提出的疑问,“你看我这个人正常不正常?”恩斯特的回答恰似一切人的心境:“正常并不意味着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哪个人是正常的。”以此,玛丽安的爱情反抗便成一种正常。
孩
“他用一个手指揉着眼睛,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他没穿衬衫,瘦骨伶仃的,肋骨突了出来,就像中世纪木刻中那些皮包骨的人像。他胸前的皮肤几乎没有颜色,并不是白的。而有点接近旧床单那种暗黄色。他光着脚,身上只穿一条卡其短裤。一头直直的黑头发乱糟糟的,从额头上披下来遮到了眼睛上,他的目光显得固执而悲凉,像是故意摆出这副神情似的。”
——第一部 · 6节
工作中邂逅的邓肯,逐步成为平衡玛丽安杂乱意识的存在。这个有点神经质的男孩,玛丽安最初有意识地排斥。好似腾云驾雾般的思辨大脑模式让早已从大学教育脱离出来的玛丽安措手不及,然而邓肯本人确定的是,就因他这点与众不同才吸引女性的目光。玛丽安对于邓肯,不是无条件地被征服,而是若有若无地在怪异心境中产生共鸣。
从初次工作访问邓肯,到洗衣房的偶然邂逅,还加上一次电影院里梦境般的相望,邓肯作为爱恋的旁枝早已美妙地伸展开来。他全然称不上是浪漫的代表,但不可掩饰的孩子气天真,恰到好处地勾起玛丽安的怜爱:
“在他身上有些地方与他孩子气的外表截然相反,它使人想起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种老态龙钟的心境是无法给予安慰的。”
他倒有意思地发言,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是南丁格尔。喜欢安抚与关爱别人。
邓肯的心境独立而强大,至于后来玛丽安与彼得订婚晚会上的热闹与喧哗,都与他无关。他像个抗拒长大的孩子一般逃离了明亮的室内,投身黑夜的孤寂拥怀。在热闹中走动的玛丽安和他有着同样的愁绪,这明明为她举办的酒会硬是找不到和谐的安身处,到处拍照的彼得像站在另一个世界,玛丽安带着对邓肯牵扯不断的情怀偷溜出彼得的家,温暖,家。
找到邓肯,是妖娆暗夜向爱情与婚姻发出的最初挑战。之前两人想发展关系,却苦于没有地方,如今的夜奔自然成为投靠旅馆的前奏。完事后的邓肯抽着烟,平静,沉稳。夜燃起解脱,散出纠缠。
邓肯郑重地认为性是成为男人的重要经历。话语蕴含的忧虑与欲念起伏不定,时时袭来。这抑或是邓肯完整的人格魅力,正好与玛丽安互补。作为一个男人努力探寻着自己在社会中的归属位置,冥冥中借助于群体力量,同时也夹杂了个体的私欲。急切找到自己,迅速迷失未来,这或许是一种半小孩化的成人反抗行为。
可要记得的是,玛丽安第一眼看到他时,认为是十五岁上下的男孩,还想其叫他父亲来回答有关啤酒的调查。细看后,才醒悟这差别。
邓肯不失平静地说,我二十六岁了。
毁
“……也许彼得是想毁了你,也许是我要毁了你,或者我们俩都想把对方毁掉,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回到了所谓的现实生活当中,你是个毁灭者。”
——第三部 · 31节
自从与彼得订婚后,她的食欲急剧下降。平常吃的食物一样接一样被自己的胃排斥,那具身体仿佛一个渐趋缩小的圆,一直缩至圆点,将一切事物排斥在圆心之外。有次去邓肯合租的公寓吃饭,为顾及做菜人的面子,玛丽安每趁谈话高潮,立马将肉抛给邓肯。这个抛接游戏甚是有趣。
无法将厌食困境向彼得倾诉,以为会自然而然地痊愈。可是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迷茫。就在与邓肯夜逃之后,玛丽安将花一下午做出来的人形松蛋糕摆在了彼得面前,同时也将反吞噬反控制的较劲摆在彼得与她的爱情餐桌上。
彼得显然没把它当成玩笑,严肃地观望,可还是心怀惧怕地逃出了属于玛丽安的饭局。
是邓肯拉下戏剧化的最后一幕。他毫无惧怕地吃完了她的蛋糕,玛丽安感到由心而发的喜悦,松蛋糕总算圆满完成本质任务。然而,当时好友恩斯特目睹玛丽安的作品后,大惊,大声说着“你这是拒不承认你的女性身份啊!”事实上,蛋糕只不过是蛋糕,满足吃食的欲望罢了。玛丽安并未盲目地烘烤象征和喻意。
她暂且成了毁灭者。某种程度上,彼得的爱情何尝不是玛丽安食欲的毁灭者?或许后者比前者的毁灭更为猛烈些吧。
邓肯全神贯注地吃,玛丽安聚精会神地看。他吃完了,说着谢谢真好吃之类的话。谁也不知道这两个毁灭者的未来,会不会温情地共枕而眠,会不会平淡地朋友相亲?
爱
化为食物的爱。有异常浓郁的香味,又能见其形。
爱从来不是吃与被吃的磨合过程。
陪你在一起,就是陪伴一个饥饿的灵魂。说爱你,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征服占有对方的全部。需要相守,需要彼此眷顾。如果有一天,眼前那人已被自己同化,那也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了。
他冷敛,丝毫不会伤害对方。一步一步走近她。她无处退却。因为爱他。所以茫然。正是茫然为自由引发导火线。你想距离,他想松手,她想高飞,我想浅眠。人都在想象,不是爱恋中人才是幻想的动物,而是人本就是很能想的动物。
于是,从享有爱,到经营爱,再到习惯爱,倦怠爱,最后放弃却依然怀念。每时每刻,无法忘记自我与身份。他还是他,她还是她,从不是你爱的那个,永不分离与永远在一起同样荒谬。
抗拒强求的爱。从食欲的生理本能出发,着实是一项挑战。到头来,精神向的爱,仍需要物质向的吃,才得以维系。
松解束缚的爱。已然由精神向下,渗透被禁锢着的食欲。在放手与拒绝间,所谓的爱,成为了所谓的自由。
叙
并不是阿特伍德初次尝试小说体裁,然而此书的叙述转换玩得着实娴熟。第一部与第三部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讲述,而占据全书大量篇幅的关于玛丽安食欲与爱情渐变过程的第二部以第三人称叙述,阿特伍德饶有趣味地进行了一场全知全能的作者介入叙述。
叙述手法还算新颖,然而轻松幽默的语言更讨巧。当时阿特伍德的诗歌已获些许奖项,小说一开始则以严肃命题探讨女性与社会,处女长篇《可以吃的女人》的语言尚未有浑然天成之境,但其先锋与锐利俨然开启女性写作另一面明窗。
整体而言,小说前半部的节奏控制欠缺火候,进入情节突变的后半部才显得游刃有余,并留下开放性的收尾余韵。随之,高潮于吞噬泉眼喷薄而不停息。
同时,阿特伍德便以此开始她“可以吃的小说”的趣味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