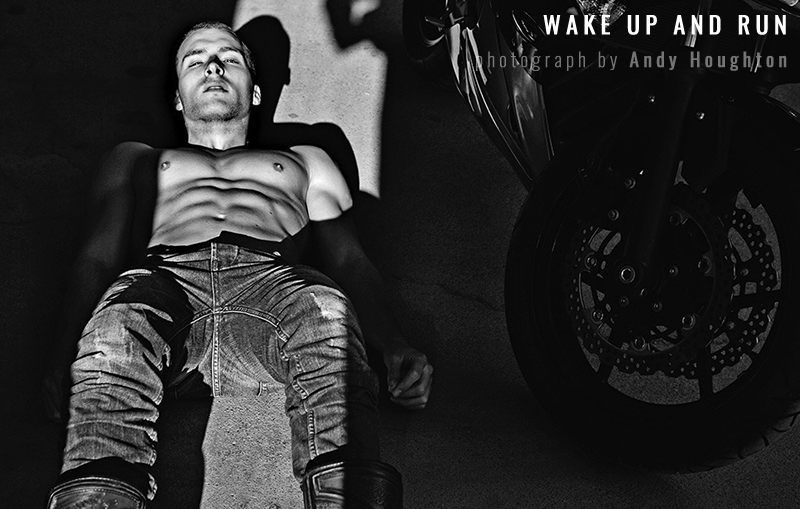01
忘记是第几次,半夜守着看长沙的夜景,说好听点而已。其实我看的是路灯。一条笔直的街被火车横碾过去,灯火由直线变成破裂的曲线,当窗口正对着街道时,才会发觉道路被灯光所染上的温暖清冷。
是进入主城区的第一道欢迎条幅。没过多久,江边的路灯与星火倒影交相辉映,说法太夸张不好,因为江水干涸了大半。然而沿江的路灯列队绵延很长,直到被更明亮的光辉湮没。在建筑群之后,会有第三队路灯填补我的虚空。道路弯曲,两行路灯交错,靠拢,叠为一体,再交错,看不明前路。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觉。
只有当真正成为“旅人”时才能体会到一个曾生活过的城市在内心所触及的无法用想念来简单定义的情绪。当然这些无病呻吟,比起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困倦完全微不足道,比起接下来将涉及到的悲愤剧透更是不足为奇。
02
没有食言。
我乖乖地把你带上车,把书皮包得乖乖的你捧在手里乖乖看了十二三个小时,在最后一次洗脸后,我再次坐下来,发现你在最后一刻的不乖。

《夺面旅人》(Every Dead Thing, 1999)当然为约翰·康奈利赢得了太多赞誉,它血腥逼人(逃跑),它精巧夺人(面目),它不讲仇恨只谈变态,它不谈希望只讲死亡,在“空虚、黑暗、死亡、虚无”的夜吟之下,找不到任何建立其上的对立面。约翰·邓恩一定不知道他为后人带来多少精神寄托和灵感源泉,不过一定很清楚何为“死寂之物”,可惜在“死寂”和另一位约翰这里,“重生”绝对不会发生,永远停在类似《圣母怜子图》的画面静谧之处。
以前的译名似乎是“夺命旅人”,听起来有点像追求恶俗效果的惊悚片,正式名“夺面旅人”改动一个字,却直接把血腥要素的最大化涵盖在剧透艺术的最小化里,当然不可否认,这个译名很艺术地吸引到了一批很无辜的颜控。其实,最初拿到书时我想到的是“面相师”系列——三本将在未来阅读的书——可惜,“面”在两者里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
说回《夺面旅人》本身,从交杂叙述的开篇起,我就不时想到迈克尔·康奈利的《黑色回声》,或者说从打算看这一本那一刻便不由自主地搬来另一位康奈利的处女作充当隐形比对。对两者的好奇和关注,不外乎它们分别为主人成名出了一把狠力,在这之外,处女作的质量鉴定似乎成了我的新强迫症。
约翰同学语言功底是强,迈克尔同学的冷硬派也不赖,在语感和氛围营造上找侧重无疑是你不爱萝卜你爱白菜。从最简单的一个层面上来看吧,即开篇,《黑色回声》虽有闪回、视角切换但总归很规矩,而《夺面旅人》则什么都来了,序幕部分梦呓叙述或称主观抒情掺杂在一只脚迈入现场另一只脚指点案件客观细节之中,两只脚换来换去,谢谢你欣赏踢踏舞。而说起第一部分,我更愿意称其为“马修·斯卡德不喝酒式之意识流硬汉侦探小说”,请重读“意识流”——我一定很久没看散文了,“马修式散文”都能轻易触动我;约翰·康纳利才不像劳伦斯·布洛克那般老怨夫般神叨叨,他更文艺,更精明,更同性恋!
什么迂回辗转完全不足以形容《夺面旅人》的第一部分,与其说这是预热还真不如用前戏形容来得贴切,左舔右吸,一到达敏感点就五六七八再来一次啦。信手摧花!
在126页时才给你来了一次爽的,却瞬即抽身,道具什么的虚拟高潮最讨厌了!而此时离第一部分的结束只有30页不到。
第二部分更是驶离主题,我们可以称之为“放松心情”,通常散步就要小心,死亡总亦趋亦步,在《夺面旅人》的“我”眼里这算什么,“我”可是叫“大鸟”,拍翅即飞再难逃也要逃掉。
第三部分进入神谕沼泽地区,混沌或者说真相已经奉上。真的,不是我们傻,就是作者傻,反正这玩意就是玩你是天真我是傻。虽然继续在大家都清楚这肯定不靠谱的边缘打滚,但好歹视线锁定了,嫌疑误导了。
第四部分太短,显然控制不住形势发展,或说不懂开发大高潮的技巧。“尾声”部分更是借景抒情之外,再无更多贡献。其实在“面对面”时,就觉着要烂尾了(现在这个肯定不是好尾),惋惜大过失望,浪费前面那么长那么意识流的铺陈,浪费这巧夺天工的夺命艺术和几近于神的杀手设定。
结尾部分的“不乖”,也可表现为我对此的“不满足”,有过一些“前科”,于是我在第三部分时就大致猜到“杀手”。而靠后一点,通篇都在围剿那个所谓的嫌疑犯,便觉无趣,这种“替身”真是用多少年都不过时。而在“真身”表现上,两位康奈利不愧是心有灵犀。美国联邦调查局应该早点关门大吉,此句无视。
至于《夺面旅人》中出现的女性,与《黑色回声》最大的区别是她并无涉案。而《夺面旅人》所出现的大量用典和玄学派诗句援引,表现足够神秘,其真实用意再单纯不过,因为书架上这类书多不用浪费,与又空又虚却又大的死亡暗示其实是矫情客串关系而已;这又让我想起迈克尔·康奈利的《诗人》里不停引用的诗句,那才是一种对死亡的优雅爱好。说到底,这些都是串场,主场不搞好,再大牌也不能生金。
零零散散说了这么些,下面集中说几点,说完我们就散会。
一、主题的虚无性。约翰·康奈利在《夺面旅人》里就像把“旅人”供奉上了恶魔的神位,也不顾对方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有“神格”,而且用极艺术的手法雕琢“恶”之无定形态,意在提醒和告诫世人,所有的一切都将逝去,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虚无。白话就是,“别瞎忙活了,等死吧。”我不清楚“旅人”那又神经又克制的思维回路,我只知道疯子的世界不是他疯而是整个世界都疯了。黑暗解剖,在“旅人”面前显得多余,因为他那么纯粹,那么浑然天成,天然到作者也不想多费笔墨展现他的“养成”,作者不解释,这更造成主题与实体间对应的“虚无取向”,没法解释,你要是解释清楚了,我们清楚了,不是你虚无,就是我们黑暗。
二、面具男的最高境界。那便是“旅人”吓唬小孩所现出的“无脸”状态。在后面也没对此作出具体解释,只好继续沿用当时的说明,那是面具的一种。是啊,面具本是一种伪装,“无脸”则是抹去各种符号各种伪饰的极简呈现,消除存在的界限,以达到最大限度混迹社群的隐身效果。多好,身为面具男癖好者的我,在此书看到此意象就已经幻想不止了。
三、同性伴侣的冷幽默。本名叫查理·帕克的主人公“我”有一个绰号,“大鸟”,但这只鸟却真的是指Bird而非Cock,让我有点失望。不过好在有另两位同性伴侣的闪耀出场,男性指数绝对二百五以上,真想把最佳配角兼最酷最好玩同性恋人奖都颁给这俩位。就以这段对话作结(老子搞这么多字全是为了引出这段话,多不容易):
路易斯和安吉尔的早饭吃得很晚。回来后,我走到他们的房间,敲敲门。好几秒之后才有回应。
“谁啊?”安吉尔嚷道。
“大鸟。你们两个没做什么坏事吧?”
“没有。进来吧!”
路易斯端端正正地坐在床边,正在看报纸。安吉尔坐在他身旁的床单上,没有穿衣服,但在腿上搭了条毛巾。
“是为了我才把毛巾搭上的?”
“怕你会自惭形秽。”
“是啊,我本来也没什么魅力。”
“有了个心理学家的女朋友还没有魅力?你也应该像别的病人一样,每小时付她八十块。”
路易斯对我们俩投来一个无聊的眼神。我发现,他和里昂还真有些相似之处。
“莱昂内尔·方特诺特的人刚刚来找过我。”
“那个选美皇后?”
“还能有谁!”
“该我们上场了?”
“今晚十点。最好把你们的家伙取回来。”
“我会派我的跟班去取。”他踹了踹床单下安吉尔的腿。
“那个丑人?”
“还能有谁!”路易斯回答。
安吉尔看着电视上的节目,“对他的相貌发表评论有伤自尊。”
路易斯的眼光落回报纸上,“鸡巴上搭条毛巾就有自尊了?”
“是条大毛巾!”安吉尔还击。
“那就未免有些太浪费了!”——《夺面旅人》, P424
补白:攻受真分明,说的是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