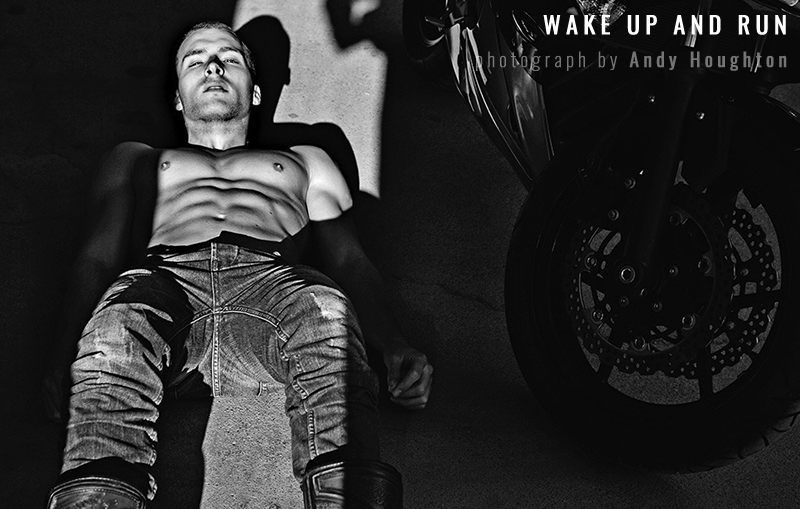01 无题
吃饭温暖上半身
洗脚温暖下半身然后爬上床——
亲吻上半身
做爱下半身
好淫荡的句子(捂脸),昨晚洗脚时想到的前半截,今早赶公车想到的后半截,天气冷了果然无时无刻不需要温暖呀!食色性也,可是绝对不能向黑泽君看齐呀!下面有请马丁爷爷……
02 访谈
上周五,九间跟我说马丁·瓦尔泽来中国了……然后我顿时惊了,我太落后啦。九间认为这也许是瓦尔泽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毕竟老人家已经81岁。不过,加快作品中译速度倒是很好的。然而马丁·瓦尔泽却十分热情,表示“《恋爱中的男人》还在译成中文,明年5月份我会再次来中国,到时候我就会选择其中的片段朗读”,多么和蔼,明年我是不是要去看您呢,明年的诺贝尔一定要归您了,要健康长寿哦。
Q:在《惊马奔逃》的《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你曾说:“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是轻的或者是重的,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示出这种共性。”在中国的十天行程即将结束,你是否适应中国菜的甜苦?
A:中国之行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无论是我遇到的作家,还是和我发生关系的交谈,这种惊喜的感觉一直是在延续下去的。至于中国菜,我觉得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大品牌,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范围去,要用北京烤鸭来取代麦当劳。如果中国人去德国,我想他们在吃饭问题上,会无言以对,中国作家到德国,我想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
Q:味觉上有共通的可能,但是,世界文学似乎面临“中心在哪里”的排他式讨论。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这之前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汉斯·约恩瓦尔也批评过美国文学,他说世界文学的中心还是在欧洲。你怎么看待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
A: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汉斯·约恩瓦尔的描述,我只能说那是非常可笑和愚蠢的观点。因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南美洲的文学发展也是蓬勃而有活力的,包括中国的作家的实力也不容小觊。汉斯·约恩瓦尔的这种观点是很愚蠢的“欧洲中心论”,怪不得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落在了一些不重要的作家的头上。像莫言,他如果和勒·克莱齐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勒·克莱齐奥可能会丧失这次得奖的机会。
Q:你和君特·格拉斯关于东西德统一后的变化有不同的看法,产生了论战,你是怎么看待德国社会的变迁?
A:我和君特·格拉斯先生关于两德统一的观点不同的话,其实并不是统一之后才发生的意见和观点的分歧,而是在统一之前已经有了这样不同的观点。在君特·格拉斯、哈贝马斯等德国著名学者看来,他们认为两德的分裂作为德国在二战犯下的一个罪行的惩罚而产生的,我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所以他们赞成分裂。但是,我认为分裂其实是冷战造成的一个后果,我是极力反对分裂的,我相信随着两德的统一,变迁的发生,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看来,德国的分裂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他们认为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以前有德意志和罗马共和国的共存,之后在18世纪的时候德意志也是被分裂为很多小的国家,直到俾斯麦才把整个德国实现了统一,其实也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但对德国的发展来说,或者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处境。如果我们无法实现统一的话,我们不作出改变,肯定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缺乏一种统一的力量的话,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变得强大。
Q: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察在德国有没有反响?德国的文学界对他的观点是否认同?
A: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想他在德国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为大众所了解的学者,至少通过我的消息渠道,我还没机会认识他。
Q:在中国之行中,你会和中国作家莫言对谈,你对这个作家了解多少?
A: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我对莫言的《红高粱》的推崇和喜爱,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流的,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我开始阅读莫言的作品,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莫言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红高粱》对历史有很好的描写和思考。还有《天堂蒜薹之歌》,描写一个只种植大蒜的村庄,所有农民的生活都是跟大蒜息息相关的。读了这本书之后,吸引我的地方是莫言在他的作品里面追求一种非常具体化的描写。现在德国作家的一种倾向是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手法去描写,莫言对所有感官的体会,都作了非常细致深刻的描述,既保证了文学作品美学的色彩,又兼顾到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这个作品读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扣人心弦,那种非常残酷的描写是能紧紧地抓住所有读者的,当然也包括我。
王蒙的作品可能更具有现实性,更接近我们现实的发展,我不能说他的作品我全部都了解,但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社会的现实应该是有很深入研究的。他的《坚硬的稀粥》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他既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手法去描写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但又保存了文学作品美学的色彩,他还运用了一些荒诞的手法,这是我所欣赏的。
Q:《红高粱》和《坚硬的稀粥》实际上和中国当下的图景有了一定的距离,你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在中国其实也在争论,一种看法是中国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来步欧美工业化的后尘。还有一种是寻找东方的传统。你认为现代化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或者还可以更快?
A: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如果由我来判断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我觉得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来到中国,不管走到哪里,感觉都非常舒服。看到的一些变化,也都是令人欣喜的,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判断: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但是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这种发展,我的身份并不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观察者,所以很难下一个定论。
在中国的旅程中,我觉得比较惊奇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文化放在了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反而去追求一种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前几天可能是遇到一个好日子了,见到了很多场婚庆活动,庆祝的形式也很西方化,新郎新娘的着装也都是西式的礼服,朋友如果去祝贺他们,也是使用英语。我们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呢?我在德国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把文化的传统好好地保留下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追问作家在哪里。
Q:在你2002年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一书中,你对电视媒体的霸权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看待作为新媒体的影响,比如网络?
A:因为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所以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体会来做一个判断。对于我来说,网络只是一个获得信息的工具,而并非是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工具。它不像戏剧或者文学作品那样,能够让人抒发自己的情感,它只是作为一个信息来源而存在,我并不认为它会构成什么威胁,或者带来什么危险。
Q:德国评价家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在评价《恋爱中的男人》时说,年龄总是让作家感到困扰,瓦尔泽晚年作品的性成分越来越多,这也许是因为越是老人,越要表现出年轻的感觉。年龄的变化,是否在影响着你的写作?
A: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尽在不言中了。虽然在《恋爱的男人》中,主人公是歌德,但是这个作品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小说,我在作品当中提到的歌德,虽然跟现实当中的歌德是一致的,但又不仅仅如此,他更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在作品里面也提到,其实人的青春期不止一个,他要经历很多个青春期。在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慕中,可能他所喜欢或者所追求的女人,也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年轻。
在爱情故事当中,年龄的差距正是导致不幸结局的因素。因为在我的作品当中,不断有男人比女人年长很多的故事,我也描述过一个女人跟比她年龄小一倍的男人发生的爱情,但是同样的,他们的这个故事也是以悲剧收场。在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奥赛罗》、《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以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作为主题的。作为一个作家,由不幸或者悲剧所带来的吸引力,是我无法放弃的。文学作品当中的不幸是很美的,它跟现实当中的不幸截然相反。现实当中的不幸,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关于“文学当中的不幸”,我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因为它不美,但是经过我描述出来,它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得美了。”比如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描述的都是不幸,但是如果没有不幸的话,他的作品就没有可读性而言。
Q:今天下午瓦尔泽先生选择朗诵《批评家之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这是你最喜欢的作品,还是最适宜在公众场所朗诵的作品?我注意到你在德国一场朗诵会上读《恋爱中的男人》,曾经多次出现笑场的情况,让很多人兴奋不已。
A:《恋爱中的男人》还在译成中文,明年5月份我会再次来中国,到时候我就会选择其中的片段朗读。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批评家之死》呢,这个很大方面是取决于技术。因为《批评家之死》这个作品已经有中文版的翻译,我们把它做成了演示文稿。因为在一个朗读会上,我觉得读者能否听懂我在读什么,这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Q/南方都市报
A/马丁·瓦尔泽
Today in History
2014 • 封面赏 | 群像绘
2007 • 钢琴少年与白兔隐喻
2004 • 说画#004 | 色彩构成的兔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