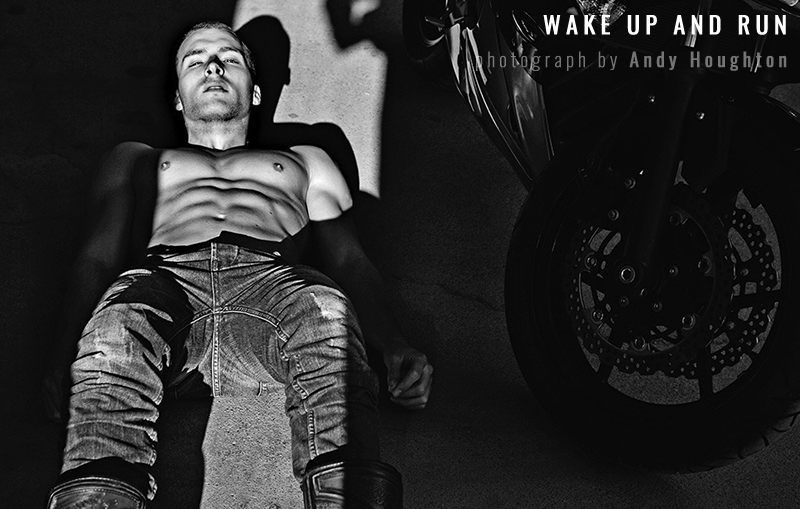by Paul Klee
往帕尔那索斯去 保罗·克利
1932年 油彩、蛋彩、画布
100×126CM 伯尔尼美术馆藏
终于说他了。尽管还有很多疑惑,我依然尊敬并且神往克利所创造的异次元世界。就好像是坚持这条死胡同一定会通向某条大道一般,在目不转睛的一二三四秒之后,小女孩为小男孩打开了秘密花园的暗门。泥土被巨人之脚亲吻,小王子的玫瑰花与狐狸私语,谁在等爱?玛丽·波平斯阿姨严肃认真的表情之下,却紧守着最幼小的欢欣喜悦。猫穿上靴子,把阿姨的下午茶洒了半桌;小鸟不甘心地追逐着他,猫瞪大双眼,却回以茫然之光。只是一场循环。鱼说,那根箭头害了我;箭头说,我只被人利用;人说,我被花朵迷薰了头脑;花说,草在帮我挠痒;草说,星星托我一个美梦;星说,太阳把我的被单抢了;太阳说,月亮要梳妆;月说,鱼跳出池塘嘲笑我。画布上的和谐不仅仅是色彩,故事的讲述不全靠线条。他说不可见,那么可见的一切都要匿形。于是,生灵们是符号,符号是意识之诗,诗是复调的空间,空间是广袤的和谐,和谐是焦虑的神经,神经是幽暗的归宿,归宿是重生的生灵。
要不停行走,不停行走,可以暂停不能倒退,才是朝圣。虽然克利的《鱼的四周》呈现最本质的因果论,但和谐却不如《猫与鸟》那般澄澈,也许直面生命之源仍需要保持静默。在同色系渐变色块的堆砌下,克利的房子有着饱和的精神、温暖的信仰与丰足的和谐。具象,非具象,由意识过度。对印象派的崇敬,逐渐被对立体派的追随替代,克利的成长过程却始终被神引领着。或者说,他力图传达某类讯息。在此,我想称他为“幽灵使者”。
《往帕尔那索斯去》继承着点彩派的技法,却明显包裹着康定斯基式的精神内涵。比西涅克更为破碎,比康定斯基更简约,线条如光那般穿梭,色块被分解,被组合,被排列,神之红日给予山峰最神圣的金色。这里是路,是路的源头。而你要去的那里,是神的山峰,帕尔那索斯。但是我很清楚你到不了。你别无他法,只有回头。当最后一本书合上时,你开始脱衣。他绝不会吻你,你很清楚。只是拥抱,却达不到热度,肉身的线条明明没有纠缠,却如浑沌的水彩画,界限突破,色块渐淡,渐淡……你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因为你讨厌他的愚蠢。热度,你要的是提升热度,要用他的体温来驱散自身的热度。没有起跑,却有冲刺。
我很颓败地靠在火车窗前,以为自己带了合适的CD,却发现只是Maximilian Hecker的Lady Sleep。请问玫瑰先生,你的花已经含在嘴里了吗?请问玫瑰先生,睡眠女士会不会翻白眼?请问玫瑰先生,你的夜晚忧伤何在?去何方,是一个问题,怎么去,也是一个问题。我很惊喜地发现Athlete的第二份作品Tourist依然延续着处男作的行走感。夜晚不会降予旅人魔咒,我刚从一场空城逃出,原来都已经散了。或者是特意为我开的玩笑。没关系,虽然没有旅行音乐陪伴,玫瑰先生的噩梦也会给我甜美的暗示。就好似克利在那幅画里暗示的阿波罗,与缪斯们,希腊诸峰的威严也立体起来,可是,在绝对平面的点之层面,梦境的讲述终将被画者所打乱,原来那宛如金字塔的符号也不过是回忆。对于克利来说,帕尔那索斯,是在记忆里的召唤物,而非虚构,梦境的烘托是全然多余。人追求真实,却被梦的意识麻痹。一个曾去过之地,还是一个未曾去过之地,这对于象征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你想探望圣地,感知路的尽头,这都是一种归宿。然而,你发出的邀请函,将你给耽搁在路口。
时间不过是二十一分钟。趴在窗台上看人群已经七分钟。你看见小学时的好友从下面走过,不禁轻笑起来,只是一场徒然的比较,你记得对方全部的笑脸与手势,字迹与发香,但早已不再是嬉戏的时候。好友拐进右边的过道,你开始哼调子。一个善唱高音的女歌手在收音机里反复咒怨着秋天,什么是遗忘,什么是平静,都见鬼去吧。你干脆坐在小柜子上摆着双腿。时间还剩不足十分钟。他要来了。我要去哪里,你责备自己。敲门声早指针一步响起。你却兴奋地赶过去开门。如此相悖的心理。
反正我迟早会出发,不如再等待一阵子。我总觉得那间有着暧昧灯光的旅馆是对自己软弱的嘲讽。可是在广场的电话亭里向别人诉说,也成为一项罪证。夜色是什么,我听见克利说,是你面对体内的幽灵所露出的狰狞。你讨厌他的身体,却需求他的欲望。只是自私的利用。他是白痴他是伪君子他是两面派他是王八蛋。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你开始把舌头当成诱饵。我开始习惯在被窝里听Athlete,将整张整张的Tourist听进睡眠,又让庞杂的Vehicles & Animals把梦带给龙卷风。记忆忽悠而去。最初看见克利撑脸颊那张顽童照时,真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画星星,画月亮太阳,画猫鸟鱼虫,画格子,画鬼。无关怪异,克利的小花园里有井然有序的世界观。玫瑰被风吹成火焰,灭了,断了,也凋落成一瓣又一瓣的热泪。鱼被解剖,猫被质问,幽灵往来,字母与花纹交换着童话。远处的山,就是眼前的风景。窗,框住了画家的想像,但不囚禁。你很害怕他不再起身,因为你承受不了他的重量。仿佛有金字塔底下的宝藏,你将头转向床面,呼吸渐渐减缓。
真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你非常不耐烦地催促他走。他很好脸皮地穿上衣服,喝了水,就走了。赖坐在床沿,觉得自己真是空虚之极。不过是一个男人身体。你同时也想到,这样也好,暂时不用与他见面。书很久不读了,老师也肯定想不到自己的荒废。不过上课日的到来,依然会让你改头换面,这才是最正常的面具。你去哪里了。我就在家里。昨天下午有打电话给你哦。在睡觉吧……等下帮我写作业。好。你眼睛怎么了。怎么了。好像一只熊猫噢。做噩梦了。还记得。不记得了。
你庆幸他并不与你同班。你也知道他原本在学校里对你的无视。但这些无关紧要。只是那张脸,与那身躯,得从视野与脑海里消失。一边转手里的笔,一边从星期一熬到星期六。学习赶不上心情的变化。我把歌词一一抄下,然后认识新单词。不会唱,只享受旋律,不能唱。天气冷了,衣服多了,我渐渐地不出去了。开始冬眠。开始结蛹。开始回忆。他们还活着,他们行走不止,男孩子们一轰而散,输者不准流眼泪。时间的催命。阳光的消毒。凉风的清扫。地球每一处都是圣地。又何必出行。
Out Of Nowhere.Out Of Nowhere.Out Of Nowhere.
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也不是的哪里。自从认同Athlete的信念,我找到了飞蛾赴火似的魔咒。三分十一秒的轻喃。宛如色彩裂变,粒子离散,身体已被散成无数无数的小尘埃。这是梦想中的图景,还是克利的视野?在类比的分层后,意识形态已经无法囊括所有的反抗,于是双向的同化将是抽象的主线。颗粒粗糙,又细碎,有缝的轨道,无缝的滑行,去圣地,去暗沼,去生,去死。去找见异思迁的脚印。去见灰飞烟灭的背影。有目的,有目的地。我们的目的无法化为动力带我们去目的地。因为意图有限,目的地无穷远又无穷近。
是虚无。是虚妄的推想。是虚空的花花世界。
任何一个思想都可以爆炸。火花。曲线。树木。垂发。闪回的光亮。在起点的时候就知道这已是一场不会有终点线的比赛。可是本能要求,应全力以赴,热情尽可释放。你,用双手拥抱,却抱得痛苦。没有隔阂了。彼此慰问,你的身体可好。第二次尝试亲吻失败,你便下定决心再也不睁开眼。瀑布坠入深潭。星星点点。残花。水。涟漪。褶皱。纹案。几何图形。被开拓的路。在最深沉的时候化为一滩幻想,随波逐流,不,无风不起浪,待在这里仅是一滩死水。向下,向下向下。交融。去最黑暗的祭坛。他不耐烦地催着你动动身子。但你只看见天花板上的那只黑蜘蛛。吐丝。捕食。我们和谐。你们不和谐。你感到沉闷,推开他的手,自己握着私处。缓缓移动,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游乐场玩捉迷藏。木马骑士感叹,你抢了我的宝剑。你不屑地微笑,他无视,他准备收拾衣物。
你弯起腿,朝他那背身踢去。不用力。他用手按住桌子,右脚撑地。根本没转身,却很大声地,说,你搞什么鬼啊。你发泄完毕。用纸巾捂着嘴,擦尽全部的气味。
吐口水。
我看见别人也拿着CD,便觉得亲切。同时也想念此时听不到的音乐。最适合旅行的一首歌。曾在很深的夜里重复着听,听到天亮了,听到机子没电了。列车哐啷哐啷地行进。我并没有前进。坐在这里。不动。被动地由机器帮我移动坐标。想念一个归宿,前往归宿。晚年的保罗·克利时常邀请幽灵造访他的小作坊,一起合作完成粗质的死亡脸谱。被俘虏,被上帝操纵,凭借他纯粹的洞察力达成与精灵媒介的生命占卜。“我为我自己探寻一个只和上帝同在的地方”,克利也希望自己“好像刚刚降生,对欧洲一无所知,也忽略了诗人与时尚,几乎就是一个原始人”。这种对本源的追溯是克利抽象精神的核心。除此之外的具象涂鸦,便成为了对焦虑精神的感性补给。我模拟着克利式的死亡玩火,只留下空洞的双眸。对面的情侣依偎渐紧。列车行进。继续。热的打火机。冷的手指。继续。接触与摩擦交换。
清嗓子。咳嗽咳嗽。
你再次拿起话筒。嘟。嘟。嘟。嘟。嘟。放下。空的房间,与空的你,十分和谐。第四次,打了。他在回避。你也在犹豫。是时候断了。在邀请与回应之间,电波不懂欲望的暗号。你到底来不来。太晚了。来吧来吧。等下吧。嘟。嘟。嘟。你望望墙上的钟。然后打开电视。
我打开网站。搜寻到乐队刚出道时的照片。很年轻,带有清风的感觉。但一切将成往事。他们体形变壮,头发留长。声线保持性感。清澈。过去的过去。将来等待将来。现在,是旅行者。在这里。在那里。在你每一个能想像的角落。狐狸衔起碎花瓣,还给玫瑰花,你的美丽裙角。猫扫过狐狸之尾,不屑地催促鸟儿去通报小王子。小王子与巨人谈论往事,烟云一般。后来,守灯人点亮灯塔。幽灵漂出玛丽·波平斯阿姨的提包,追逐着火焰。火焰热恋着玫瑰。还好小女孩适时将花园开放。小男孩疑惑地看着扭曲的树,好奇地靠近了树后的男人。鱼吐着抱怨,被月亮听见。男人露出孩子般笑容,轻轻放下画笔。可惜,猫与幽灵嬉戏,将调色板糟蹋。色彩,色彩混杂。流淌。越界。交融。万千华彩。
你在门口听他上楼的脚步声。声声呼吸。开门关门。步步跟随。脱衣穿衣。慢慢温暖。多话寡言。借与索取。再见再见。开门关门。闭眼闭眼。后来,你把电视关上。只有指针走动的声响。纯粹的时间。睡一觉。你十五岁。少年无情事。
我下火车。随人群而去。嘈杂,气味,混乱。我在这里。这里不是哪里。还活着,还睡着,再随公交车去暂时的归宿。太阳呢?要等待明天。在我的小被窝里,听Athlete带我重返旅途。但是却迷失了。我看见你在前面伫立,微风,与瘦弱的身影。有如克利的小生灵。线条尖锐。色彩浑浊。我从身后抱住了你。静静呼吸,体味弥漫了那个午后。
我要去帕尔那索斯。你去吗?
你很坚决地拒绝。我相信你的内心温暖。如昨日夕阳斜影。
12/08/2006
Today in History
2009 • 换装
2008 • 独二无三
2007 • 夜夜夜贼
2004 • 暖冬飞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