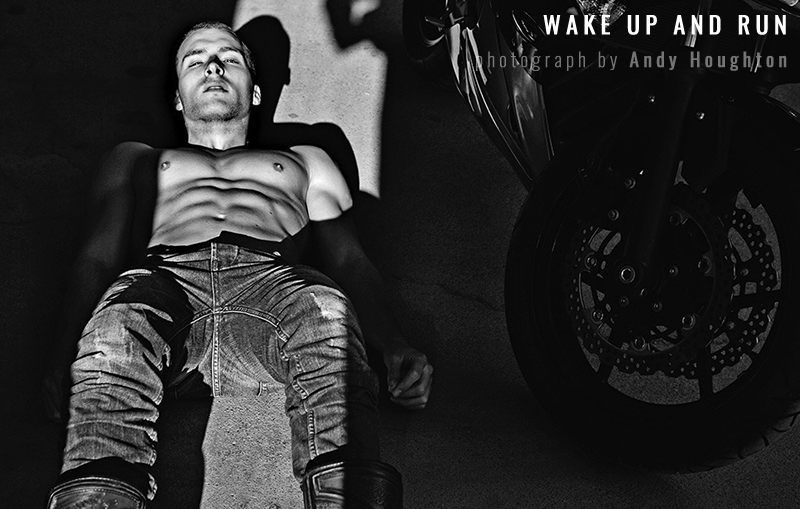那最后一锤《萨罗,或所多玛120天》的动静足够大,可怜死后的帕索里尼依然不得安宁;本想隐居的乔治·梅里耶被小男孩雨果撞醒了往日的梦,星月披风温暖又拉风;风度不减当年美少年的故友来到面前,把往事、计划、个人陈述杂糅在一块细细道来,“怎么?你竟然会在这种地方?”;同样的惊喜存在库切化身的老人心中,却学着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将“老人与性”掩在文论琐碎之下,还有结构的幌子,不愧为老无赖……在大师手中没有天堂,只有内心世界。
一份自白

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的自恋程度在小说扉页引用的夏多布里昂名言中可见一斑:“在描绘他人的心灵时,我们其实只是在描绘自己的心灵。”于是这本名义上替电影大师P.P.帕索里尼作心灵传记的《在天使手中》实则是费尔南德兹的内心抗争史——相同的同性恋身份让他能更好地揣测帕索里尼的所思所想,可是,“子非鱼”的困境大过“你们都是好同志”的乐趣,所以这部洋洋洒洒近五百页的小说始终是个“伪传”。
不过,也正是虚构柔情交织在诸多真实人士、现实事件当中迷倒了不怕好奇杀死自己只求爆料来得更凶猛一点的读者。第一章节,事无巨细地交代P.P.P.(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早年生活环境,第一人称却心态苍老地吐槽“我,我这个最‘各色’的人,害群之马,不入册的贱民”,然后自白完毕;第二章节,本着二元宿命论的和谐精神,来了一番对名字/身份的宗教解说,皮埃尔(Pier)与彼得(Pierre)实际是同一个词,于是彼得与中间名保罗的抗争开始了——彼得保守中庸,保罗焦虑神秘爱走极端(关于名字的这一章的虚构套设现实是全书最出彩的,由此也衍化出帕索里尼的两面性,彼得对应天使,保罗对应恶魔,也许互换也行?);第三章开始絮叨P.P.P.的童年,小说情节才算正式开始,作者的巴洛克笔法让人纠结往复在细节与细节的落差上,真正的故事段落其实很易读。
撇开巴洛克,看看本书主要的炒作点(失礼了作者本人极讨厌炒作,人称“无视荣耀”)——P.P.P.的同性恋身份,本来也没什么,可却因为恋童什么的惹来官司,这就把问题搞大了。考究此倾向的原因,还怪P.P.P.小时候被父亲吓得把自我身份认同为“一名女性”,毕竟P.P.P.认为“我生来却是为了温柔,为了平和的”。随后他在磕磕绊绊的青春期中重新审视了自身对男女的不同感觉,“拒绝女人,却欣赏女性雕像”差不多成了一具指南(男)针。
延伸到第二部,P.P.P.多次表露出对青春阳刚俊美的“小伙子”/“小子”的热情。因为第一次恋童无果的惨淡,他还一度把“感情”打入冷宫,觉得每次与陌生人寻欢就够了,关系的把持太伤人心神,何苦呢?其间,政治见解、小说电影创作与之同步,彼得指引着他向这个外部世界的一点准则和秩序靠齐,保罗又把他拽出去,拖到一个不似凡世的圣山上探险,或在荒芜河边与小子们撒野,清醒与混乱抗衡,清净与糜烂交融。P.P.P.虽时刻盯着自己的左眼皮是否垂落,却不曾发觉把画中的左右弄反了,这长长的伏笔也昭示了后面的悲剧结局;也许那并不算悲,是P.P.P.的自我解脱,如此勇毅。
小说有一个倾诉对象,“你”,杰那里埃罗,P.P.P.的理想爱人,但这位理想爱人结婚了,光留下P.P.P.在自个儿意淫对方和妻子的婚姻生活;这个“你”也没什么出场戏份,它更相当于一个收信人的角色,把读者拉到深情叙述者的对面,听他倾谈,絮叨过往。
P.P.P.在“你”身上所找到的安宁,却是死后所无法相比的。
一个梦

此雨果非彼雨果。维克多·雨果无意瞅见圣母院墙上手刻的希腊语单词“命运”,然后写出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这应算异常强大的脑补能力,或说造梦能力超凡;至于现在说的雨果只是一个叫雨果·卡布莱的小男孩,怎么能与大文豪相提并论,虽然他也很爱做梦,可惜做梦只让他去做贼,这让写书的雨果情何以堪……
同名狡辩到此打住。雨果·卡布莱没啥出息,仅有的长处是跟着钟表匠父亲学会的修理才能。在太阳八九点钟的时候溜到玩具店偷零件有点无奈,更苦脸的是被玩具店老人逮个正着。为什么要偷?我不说,我就不告诉你。老人扣下了雨果的笔记本,雨果索求无能几乎泪奔而出。被老人收养的小女孩名叫伊莎贝尔,表面文静,实则热情似火,她主动搭讪雨果,“你是谁?”雨果说出“真相”,“你爷爷偷了我的笔记本,我不要回来,他就会烧了它。”女孩阻止雨果丢小石头的手,“不能让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你为什么想要回你的笔记本?”雨果嘴硬,“我不能告诉你。”他还想捡石头,却被伊莎贝尔推倒在地,无法动弹。
再后来,女孩帮雨果搞到了笔记本,雨果却又偷了女孩挂在胸前的钥匙(其实伊莎贝尔这把钥匙也是偷的,这两位彼此彼此吧),女孩发现后很生气,“我都已经帮你了,为什么还要偷我的钥匙?”后果很严重,女孩这次把雨果压倒在了地上,用膝盖顶着他,雨果疼得大叫。
可以说,在偷来偷去、推来压去的过程中,两位小主角的活泼形象早已跃然纸上。
雨果偷玩具零件是为了修一个神奇的机器人,雨果努力把笔记本弄回来是因为机器人的图解都在那上面,而老人为何一翻那笔记本就执意把它扣下来,这才是本书最早且最重要的伏笔。《造梦的雨果》是对早期表现主义电影先驱乔治·梅里耶(George Melies)的致敬,而玩具店老人便是他在本书中的化身,他对雨果修理机器人的百般阻挠与其说是一种执拗,毋宁说是一种坏心眼的调戏;笔记本不是不给你,你先来店里帮忙补偿以前偷东西的损失吧,笔记本不是不给你,而是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喏就在手心的这一包里。
雨果很有坚持,这真难能可贵,即便没了笔记本的图示,他也要凭记忆来把机器人修好。而机器人正是通向乔治·梅里耶的电影魔术门。那些黑白的却闪耀着奇异想象光芒的剧照插图一帧帧扑面而来,往昔的欢乐与雨果眼前的困境扭动不止,不成舞步,最初梦想或想象的启示,随着年岁的渐长才能渐渐发力,把那些动不动就被推倒的孩子气转变为独当一面的沉稳。
《造梦的雨果》让人褒奖的是书的形式美感,文字只占一小部分,大量素描、电影剧照、摄影图片的融合使得本书更像是绘本,但碳笔素描明显带有电影镜头推移与分镜的效果,加上页数过多、主题稍显过重,其实并不适合儿童阅读。
而让人诟病的大概也是这种表现手法,有时候文字留白的美感足以让人回味,紧接而来的图画扩充则会破坏这种留白;有时候连续插图的衔接上略有重复,不太有动感,而真需要有动感的地方却一两页带过(比如说老人披着星月披风与雨果回家一幕)。但开头结尾真的很美,圆月慢慢从画面正中央到画面右上角,慢慢变小,直到下一页的太阳升起,雨果的侧脸赫然出现,一本正经;占满两页的巨大圆月,慢慢被阴影遮蔽,慢慢变小,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十分之九,一团黑影,然后“剧终”。
一种述怀

十年前,大江健三郎在那本砖头般厚的《空翻》里反复援引R.S.托马斯的诗句;而在这本于2007年冬出版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以下简称《安娜贝尔·李》)则反复引用爱伦·坡的诗句,“每当月泛光华,我便梦见优美的安娜贝尔·李,每当星辰生辉,我便看见优美的安娜贝尔·李明眸闪烁……”诗情为小说注入一种朦胧的特质,断断续续的诗句引用伴随着追忆往事在过去与当前来回跳转,很有逝去的惋惜之感。
作为刚写完“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不久的大江,自己也格外清楚,有可能这将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想当初,出版界不还把那本《别了,我的书》冠为大江健三郎的封笔作嘛),《安娜贝尔·李》与那三部曲的不同显而易见,它短小、轻盈,虽然同样带有自传色彩,但大江本人却在叙述中抽身以观他者,连续絮叨的长篇对谈不如说是单个人物的自我解说,前引号跨幅很大,如果能忍受此般个人性质的吐槽,那么《安娜贝尔·李》其实很好读。
正在与儿子光进行行走锻炼的大江,邂逅了一位故友,“怎么,你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故友木守开始表达来意,他再度令大江回想起来那些从前的事和从前念叨的诗,三十年的时光在两位老者的身上映照出尴尬和窘困,而这些与另一位名叫樱的演员朋友有关。
序章之后,即迈入回忆,樱随着木守一起出现,他们打算拉大江加入一个“世界级”的电影拍摄计划,那时已是小说家的大江从未尝试过电影剧本,却因为某种与樱的奇妙缘分而应允下来。之后小说情节随着剧本情节推进,着重表现大江所赋予剧本的内涵延伸;有关樱的过去,种种暗示与言谈也渐渐出现,而这种暗涌到了后面就与剧本里的悲壮之情融汇成绝望高潮。
小说中的木守曾如此评价大江,“无论怎样的小说,这家伙都能按照自己的风格做有趣的解读并重新叙述”。《安娜贝尔·李》的主体追忆部分围绕着那个剧本,看似在解读剧本,实则是在解读小说主角——樱,樱的形象基本在他人的言谈和观察中得以展现,她的正面描绘其实不多,更像是爱伦·坡诗句中化身现实的安娜贝尔·李,优美且颤栗,绝望却饱含爱意。
在后半截,剧本相关解读已经淡出,樱把从剧本里感知的精神过渡到现实当中并点燃这新的“绝望中的希望”。大江衍化的剧本恰成一块通向樱内心世界的敲门砖,在不停借用不停述怀的过程中,它也随着传奇少女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般逝去,至于来来回回三十年时光,开始又终结于一句富有意味的惊喜搭讪,“What!Are you here!”星辰闪耀,在音乐寂静式喧嚣当中,她的回音无息荡漾着,一切疑虑都没有答语,一切暴动皆会复归平静;月泛光华,在“哈、嗯呀——考拉呀”的吟唱声中,故事登上情绪渲染高峰,随呐喊宣泄而出的痛楚必将会与记忆凝在一起,直至逝去。
一场对照

写《长恨歌》的王安忆女士有点疑惑地说库切的小说(无论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其全部意义都归结到性,“风土人情,性和暴力”,令人堪忧?的确,那本《耻》把这三个元素肆意发挥,却还获奖了,真不可思议。《耻》在他的作品中自然不是最好的,所引发的话题确是最有争议的。相对来说,2007年的新作《凶年纪事》要温和许多,虽然按照那说法,本书终极意义和《耻》同样归结到“性”上,但《凶年纪事》那纷杂琐碎结构将这一主题消解了不少。
全书分为“危言”与“随札”两部分:“危言”侧重政治、社会等热点问题,收录31篇很有个人见地的短文,小标题多以“论”打头;“随札”共24篇,十分随意散漫,从梦境到环境,从老年困境到文学艺境,信步闲庭。
《凶年纪事》让人称赞的结构并不是这论文与随笔的划分,而是每一页的分栏:“危言”头五篇分上下两栏,上栏是《论国家起源》《论无政府主义》《论民主》《马基雅维里》《论恐怖主义》,下栏是“我”的视角,叙述从洗衣店起邂逅的一位姑娘;从“危言”第六篇《论制导系统》开始变为三栏,之前的下栏“我”的视角移至中栏,下栏变为那位姑娘安雅的第一人称叙述;“随札”的头四篇《一个梦》《“粉丝”来信》《我的父亲》《听凭天意》虽维持着三栏的结构,但中栏已留空,到第五篇《公众情绪》恢复。
抽去文论随笔部分,《凶年纪事》只相当于一中篇小说,主要人物就三人:“我”,一名移居澳大利亚的知名作家,年逾七旬;安雅,曾当过摄影模特的女子,她口中的C先生便是指“我”,应C先生的邀请替他为书稿打字;艾伦,安雅的爱人,一名投资顾问,有点傲慢。
上中下栏的交替必将制造阅读的衔接障碍,这才是库切的本意,如果系统地分别将“危言”、“随札”、中栏和下栏从头读到尾,那么分栏的意义荡然无存。
C先生一登场便是一副“意淫”心态,他眼中的安雅带有恬淡的性诱惑;“凶年”是指外部世界的局势,对于C先生来说,身处老人的窘境并梦见死亡才是凶之所在,“老人与性”是本书的两大主题,政治杂谈成了点缀。
中栏是C先生与安雅的谈话,视线落在安雅身上,安雅在此提出对文章的某些看法;下栏几乎是安雅与艾伦有关C先生文章的讨论,艾伦的某些强硬逐渐凸显出来。这两栏映照着上栏“危言”的某个名词、某些观点、某类现象,并直接引发了“随札”的出现——安雅对C先生说,政治没什么好说的,你不妨写点别的,鸟儿呀梦呀,随意一点。
“随札”的出现,意味着C先生心门的打开;“危言”从始至终都有点拘谨,在后来被艾伦大肆驳斥,到了“随札”后半部亦即全书的高潮处,会发觉前面约三分之二篇幅的“危言”正是因为这个反驳、讥讽的不同声音而变得别有存在意义,“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危言”太上帝视角太自持清高不是来搞笑的,而是等这一巴掌的快感,于是说每一本书都要换个写法的“翻花绳先生”库切异常精明,他不会等着被众读者来扇耳光,他更倾向于自打脸万万岁。
在“随札”的临近尾声处,上栏依然是C先生的我思我感,中栏变成了安雅的来信,涵盖从小说一开始的孽缘到当下的生活报告,下栏有一长段变成艾伦对C先生的言说。三种声音的鼎立局面,促成《凶年纪事》分栏意义上的高潮来到,在此之后,艾伦言毕,安雅的声音便重回下栏,与中栏安雅来信一起翻至小说最后,故事终了。
至于时刻影射着库切本人的C先生的结局,却归结到文学终极技巧上,不得不说一声库切先生您野心真大啊。
07/02/2009
Today in History
2013 • 枕边微光#041 | 窥梦者日记
2008 • 周末提前一天
2007 • 马赛克式意识流
2007 • 叁年志 - issue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