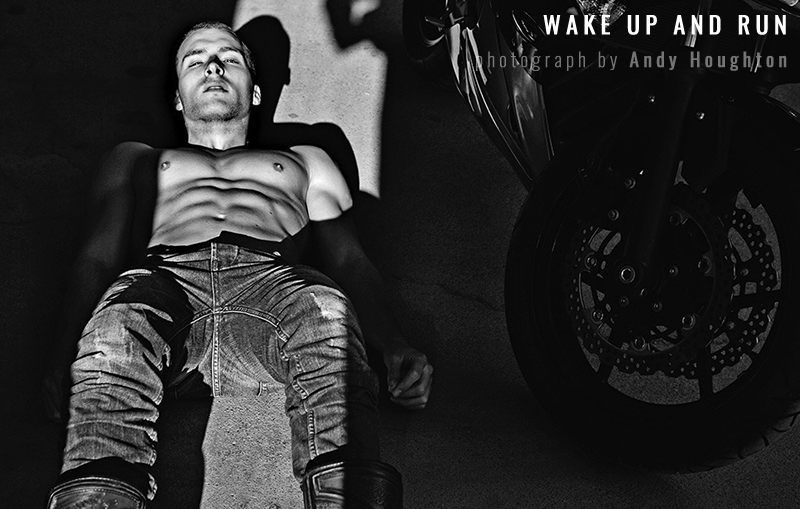这世界有太多平庸,所以我们寻找刺激;这世界有太多刺激,所以我们苦求平静。在奇妙与奇迹之间,只差一个扳手,看它能否将星火弹上夜空,然后绽放宇宙般绚烂的无穷无尽。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只好躺下来,感受夜色满溢的清凉,遥想如果跳上马戏团的列车去流浪会有多精彩。假如游遍世界,会不会找到地球的按钮,摁一下,雨落雪纷飞,再摁一下,四季切换山河变脸。是的,一切皆在想象中,梦境的真实让人直叹现实的无奈,然而想象这种无需任何成本的能力简直就是人类创造美妙的专利。少了它,世间将会多么了无生趣啊!
帐篷之内

夜晚的帷幕缓缓落下,之后似乎再未被拉开。讲故事能讲到让人忘记时间存在感的地步不能不说是高手。除开部分典故或术语造成的间隔及部分配角展开过往支线添加的繁复,《马戏团之夜》整体显得格外流畅,就像那座神奇的座钟每隔一小时就敲响十二下,故事源源不绝地从永恒之夜一涌而出,令聆听者惊奇感叹。
原本是简单的记者采访,被拉长成为马戏团舞台背后的世间奇妙物语。而记者华尔斯也逐渐坠入女飞人的魅惑之中。这位空中飞人有个名副其实的名字——“飞飞”,象征着她肩后的一对羽翼。这一奇妙事实也颇受争议,她到底是打着翅膀噱头的尤物,还是坠落凡尘的天使?真相没几人能看见。可知的仅是,没有翅膀的飞飞只不过是身材相貌均一般的平常女子,有了那对翅膀即便走在钢索上不够轻盈也足以迷倒全场,要不然她怎会被称为“伦敦维纳斯”呢。所谓的采访是要挖出独家爆料的幕后故事,华尔斯不疾不徐地走进飞飞的过去,深入到以至于要跟随飞飞踏上马戏团横穿俄罗斯的冻土之旅。给老板的借口是隐名埋姓呈现马戏团圈内人的报道,而在飞飞面前又彻底变成了小丑,而且是受伤战士型的小丑,他无法阻挡自己堕入爱河,也无法逃开随后万劫不复的深渊。
《马戏团之夜》的野心在于,用传奇的手法写爱情,以爱情的语调写奇幻。哥特式氛围不时渗出,魔幻写实也煞有其事,女性主义的魅影频频晃动,而像矮人、四眼人、睡美人、双性人这样的奇人异事则统统塞进了马戏团这只魔桶里,随着乐团的欢鸣一滚一滚地上路了。个中细节表现得十分详尽,马戏团内部的等级划分,舞台明星的辛酸往事,笼中动物们的躁动与慵懒,像万花筒般旋转变幻着讲述方向,在这之中,始终不变的是对飞飞的聚焦。一如探求神秘那样乐此不疲。
第一部“伦敦”是个人小传,飞飞坐在幕后伴随着长夜将往事娓娓道来,可夜色一旦搅拌进来就让种种追忆变得亦真亦幻。奇迹摆在面前,人总不相信,总带着怀疑眼光试图看透一切。可有些事情无法被验证,只能要求你相信,就好比剥开了一切后,花的美好也不复存在。华尔斯在后两部“圣彼得堡”、“西伯利亚”的奇妙旅行中飞速成长,从备受挫折之中爬起来,带着可望不可求的爱慕大声喊叫起来,甚至遁入神游冥思之境,万物伊始,仅是虚空。
说到底,马戏团这一存在本来就是梦幻的象征,它将人们对奇妙的种种欲求集中绽放在光影舞台之上,在音乐的催眠中表现自由,在舞蹈的滑稽中拥抱流浪,整个团队的行进状态也是在追求冒险。可是有个窘况是,他们能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而又有谁能去逗乐他们呢?就如小丑抹去一脸古怪后,只剩下疲态。
宇宙背后

要说起上帝视角,没有比米歇尔·法柏的《玩具故事》更好玩的了:上帝独自玩耍,他住的地方没有孩子,也就意味着不必与人分享在废弃的宇宙后面找到的好玩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后来,上帝找到一颗行星,把它带回家吊在天花板上,躺在床上凝望蓝绿星球时,上帝不知不觉睡去,梦见自己变小后在这颗星球上旅行。但梦终究是梦,不管上帝多么为这颗星球着迷,他始终被摒弃在外,行星自身的生态系统圆融完整,无须任何外来力量介入。上帝长久凝望着它的美丽,倾听着那些细微且从不重复的声音,以为自己多了解星球上的生灵故事,却不过是一些假想而已。上帝想体验星球上的美好,却只能可怜地做做梦。
当然,这本收录15则短篇的《雨必将落下》并不全是童话故事,只能说幻想作为一种尤为珍贵的介质让故事格外闪光。同名小说(亦即开篇故事)《雨必将落下》有种步步逼近的节奏,如同那必将落下的雨,不可逆转的时间,真相最终会被挖出来。成人世界的纠葛罅隙自然会给孩童施加影响,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正是在伤害过后起修复作用的心理治疗老师,她安抚孩子们的心,也慢慢引导他们正视已发生的事实,那个教室里的惨案逐渐被还原出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她和孩子们都无法预知。事情总是这样,刻意逃避和刻意忘却都会有反弹效果,顺其自然也许是最好的办法,阴霾总会过去。
据说米歇尔·法柏从德式摇滚乐中汲取灵感,从这些短篇小说看来,幽默气质无处不在,时隐时现的浪漫细胞也非常迷人。《鱼》是鱼游天空的末日世界,《传话细胞》能让咖啡、热水等长久保温,《胖小姐和瘦小姐》从常态出发向两个极端发展,是寓言也是无可救药的悲剧。
《尼娜的手》换成了手的视角,带领读者去流水线的工厂参观,也带着读者探访天空、岁月流逝、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体验数不清的感受,最后重归平静、麻木、黑暗。《帐》是一个少女的异想天开,她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寄去一笔请求支付的账单,自称在太空马桶领域很有研究顺便给出了最佳解决方案,事实是她只不过反复阅读《怎么会和为什么》科普丛书罢了,可最后信上的认真语气令人忍俊不禁。
其实每篇的风格基调各不相同,一篇篇看下来就像一次次从现实跃入梦境,再从斑斓梦境走出来那样,氛围烘托极为到位。《雨必将落下》的心理描刻,《鱼》的毁灭危机,《温暖又舒服的地方》有青春期萌动,《爱的隧道》里那被物质化后的感情碰撞,都可圈可点。
至于最后一篇,《羊》,那简直是怪诞与另类的大聚会。五位艺术家收到邀请函,前赴世界另类艺术中心开会,结果被甩在苏格兰高地的某村庄前,每人收到一封署名为“一名艺术爱好者”的信,五封信把五位艺术家都批了个体无完肤。而看看周围,这所谓滋养艺术的土地,远近都是羊,艺术家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羊。就连骂这该死的骗子,随时都有一声“咩”附和一下呢。
梦境边缘

奈瓦尔的主要身份是诗人,其浪漫象征主义诗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波德莱尔、兰波等人莫不从中受益。他在剧作和小说上的创作为数不多,加上后期癫狂病症的加重,使得创作愈发艰难。这本《火的女儿》算是他的小说精华之选,收录了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其中有原本是长篇小说《假盐客》写作计划的《安婕丽嘉》,还有更具影响力的《西尔薇娅》。
不过在此,主要来关注一下奈瓦尔的遗作,《奥蕾莉娅》。这部中篇小说写于最后的疯病时期,最后直至奈瓦尔离奇上吊自杀,本作也没有最终完成,留下了大量笔记及修复异文。至于作家本人的离世,也成为了文坛的谜案,没有人清楚奈瓦尔最后的精神状态,这种解脱方式是不是本人的选择也无人能知了。
从《奥蕾莉娅》可以窥见一些真实,而这种真实却是相对于现实的梦幻真实,一种虚构、臆想的真实。因为奈瓦尔在一开始就主张,“梦是一种第二生命。”他强调并放大了梦对人的驱动力,通篇写作也像是在记梦,偶尔夹杂的现实叙述也变得如梦似幻起来。也正是如此,自我潜在梦幻之下,变得轻盈,在梦境的沉溺下追求双重意义,在幻觉的渗出中体验现实的境遇。大概没有人能悟透奈瓦尔的梦境所指,那些创世纪、精灵神怪、宗教神游、日月星辰之蜕变,还有那些稀松平常的田园生活是如何变成了忏悔不止的精神桎梏。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最后的疯狂也造就了这番文字上的狂欢盛宴,而现实之惨淡不能不让人扼腕以叹,“奥蕾莉娅”暗指奈瓦尔的初恋情人简妮·柯隆,她与他人结婚给奈瓦尔带来的失去表现为《奥蕾莉娅》第一部尾声对梦中婚礼的双重抗拒,她的去世则意味着第二次失去,于是第二部里满目的诘问与自责更像是领会了奈瓦尔本人的谵妄颤动。
不管如何,在不同梦的游荡与渗透之中,都不会有太阳的出场,万事万物仿佛自身闪着光亮,而这份缺失也造成了梦境世界的一种失调。梦境的模糊本是正常,而在模糊世界里找寻炽烈的原初之火,像是刻意去破坏梦境的常态一般,奈瓦尔的写作显然十分清醒,虽有大量梦幻呓语,但始终保有一份自我本真,它披上双重外衣,与梦说梦,在虚无缥缈之境戏弄着那些阴暗模糊的奇形怪状,最后等待精灵世界的洞开。
迷宫深处

故事概括在本书面前是苍白的。《在迷宫里》就像是没有情节的无声电影,黑白画面跳接的一些看似重复的片段。一名迷路的士兵在小城里兜兜转转却始终无法抵达目的地,雪始终在下,引路小孩跳出来又很快消失,士兵挟着包裹却几乎忘记自己的运送使命。画面、场景反复出现,他的前行绕着圈子,也像在迷宫拐角处撞壁然后又折返了回来。
他反复问路,却忘了路的名字,连核对路名时也不大有印象。他反复撞见那个在路灯下出现又消失的孩子,并怀疑正是这个孩子将他领到了那座咖啡馆。他一会儿在室内一会儿在雪夜里赶路。他在黑暗的走廊、楼梯间摸索,在假兵营寝室里寻找出去的门,他干渴,他忍住干渴又奔赴上路。他在矛盾的四岔路口踟蹰不前,他在路灯下凝视雪的颗粒状态。他在朦胧中睡去,他独自一人呆在室内不受风雨的侵袭,却能感知到外面有人在雨中赶路。
格里耶本人在《在迷宫里》的前言中提出“这个叙述是一个虚构,不是一个见证”,偏离了现实,士兵的身份也变得模糊,正如他那明显缺失编号的军大衣。士兵的形象也化作一个符号,代言使命的前行者。围绕士兵的周遭也沦落成了虚构想象中的意境营造,那时满时空的咖啡馆,周而复始的四岔路口,雪停雪落的街道,以及那永远黑暗的室内,都像是被刻意安排的场景。而所有人物也被刻意抹除了身份属性,单剩下孩子、女人、军人这些泛指的形象,他们就像光有轮廓并无本质的影子游荡在士兵的梦境里。
是的,梦境或许才恰如其分地映衬这座迷宫之城的种种非常态。在小说最后,有真相揭露,士兵因为孩子的鲁莽而引发占领军的射击最终腹部中枪死在了女人家里,那个他最后坚守的纸盒其实是一些私人物品。于是在此之前的全部叙述就变成了士兵临终前的幻觉描绘,或是死后的魂游之旅。就如那部有名的电影《生死停留》(Stay)一般,死前的执念让故事闪回,一瞬却徘徊在永恒之间。
看过结尾再回到开头那繁冗、冰冷的描述时,就会对这种莫名变更的视角、莫名切换的场景多一分了然。挂在咖啡馆墙上的那幅画,集中描摹了整个故事的形貌,士兵的形象、环境的具象仿佛都从画框内流淌出来,渗在整个黑夜世界里,那么富有动感,却又始终维持静态,永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