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头再联系。衣服穿好后就有了一种抗拒感,他觉得不会再有另一个夜。送走来客,送走过去。他想睡个好觉,不被任何人打扰地睡到午后。打开房门,打开呼吸。正要贴个请勿打扰的告示牌,做作之举连风也嫌弃。他被关在房外。室内的电视继续喧闹竞赛,一楼的麻将如火如荼堆砌。他缩在楼梯拐角处的板凳上,尝试睡眠,未果。夜里一点,街上仍有夜宵摊在营业,车辆几乎没影,是漫步者的王国。他走到熟悉的小巷入口,迈进黑洞。这里有道上锁的门,毫无意外。他离开,去一个相对温暖的地方。他奔跑,与过去的暗影迅速擦肩。那里是哪里,那里是尴尬的观影场所,那里是奇怪的翻滚房间,那里是稀罕的购物体验,那里是日常的漫画蜗居,那里是裸露的勒索阶梯,那里是短暂的陪聊分岔,那里是也许会有明天的上升坡道,哪里是那里。哪里都不会有重播键。快餐店的背景音乐整日无休,他趴在靠窗的角落,听乡音与普通话之间的诡异交谈,两腿些微哆嗦,没穿袜子的脚互相磨蹭,怎么看都像是刚从梦游中醒过来的打哈欠者。可是,这个打哈欠者并不会有那个心情列表一二三,构想无数个“你”,他只想音乐停止,交谈停止,走动停止,灯光暗下来。困倦与寒冷持续拉锯,他在一团漩涡里耗过了数不尽的流行曲,甚至有让他诧异竟然混进这首歌的自语时刻。外面天色依然没有变化,他觉得过去了很久,但其实只有一两小时。最后他向门口的那个女孩问话,现在几点钟了,对方一脸不解,他只好再用普通话缓慢地重复一遍。
谢谢。他推开门,早起的车辆是苏醒的前哨。匆忙跑回黑洞小巷,门依然上锁,他前后敲了几次,毫无动静。过后一个扛着麻袋的男人走下来,有点奇怪的眼神,一言不发地找出钥匙开了门。他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上楼。
整栋楼仍在沉睡。他碰巧看见灯火闪烁,叫唤了一声。是谁。是……他把名字说了两遍。第二道门的打开,对他而言意味着这趟意外漫游的终结。他简要讲述经过,省去奇怪的冲动,省去无关的细节。用热水洗了把脸,终于躺下来。被子盖在身上,格外厚重,他尽量不去琢磨房间的气味,不去计较逐渐成形的轮廓,在时响时停的寂静中努力入睡。
鬼先生与无梦一起降临。
歪头,微笑,打着问号。鬼先生脸上画着咧嘴,口里却说着“你是认真的吗”,总有办法让他卸下心防。他恨安静带来的孤寂,他恨虚幻带来的慰藉,他对当下抱有疑问,对以往怀有眷恋,他不再期待,不再恳求,鬼先生所展示的惊喜。童话终有一苦,温暖总会冷去,他不再嚷着存在虚无相信绝望梦想爆裂清醒混沌界限规则意外确定你好再见,但他始终对拥抱难以抵抗。这是奢求。鬼先生对索取并无回应。他无比自私地百般尝试,把过往的讲述重述,故事并无新的延续,秘密还埋在小镇外的树林里,手头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也终归是个玩笑,而非魔咒。点头,饥渴,标上句号。鬼先生张口欲言的模样,总能治愈他的无聊,他等待着沉默被插入填充,可是除了鬼先生简单的几句问候,没有更猛的新料。是,空洞一直都在,缺席几年不过刹那。不是,移情借口是麻痹良法,缺席几年不过是养精蓄锐。他对质问没有说辞,闪躲转移,生怕在一个坑里栽个没完。鬼先生一脸诚挚,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任何玩笑都不是玩笑,鬼先生一脸面具地问,
年更君,还记得当年教给你的隐身术吗?他一脸茫然,反说鬼先生并没有教过,不管他多次哀求,被拒的心碎让他想起克利的抽象画,在回忆里打转没有去路。鬼先生此时坐在他身旁,手掌叠在手掌之上,温暖向下。
故事向后。
三年前的四月,鬼先生在列车上遇见了一个戴着奇怪兔耳的男人,他们面对面坐了约摸三小时后开始交谈。男人自称R,刚搬离废柴镇,打算四处游玩一段时间。鬼先生邀请R到自己的木屋作客,R欣然应许。在小屋的生活,惬意随性,R认识了离家出走的熊,他们三人一起睡在鬼先生那张硕大无比的木床上,彼此闲谈,时间线精简又乱序。鬼先生做饭,熊先生跳舞,R先生只喝茶。茶杯是鬼先生亲手烧制的,印花正是这间木屋。后来,R带走了这只杯子,后来,R在某天马戏团散场人群里最后一次看见熊,后来,鬼先生打着哈欠拍拍R的肩膀,劝说着安定下来会更好,最终离开了木屋。R会定期寄来明信片,尽管鬼先生换过不止一次住所,纸上风景虽好,却比不过背面的
黑暗的地板上微闪着蓝光,手臂垂下去,摆出画作的姿势,终究是伪装。他翻来,车鸣试图与心跳保持同步,他覆去,念想堆积与计划出入太多。屏幕上的信息止步昨日,他摁下台灯,仿佛一点光明就可将他从不完整中拯救过来。鬼先生说这是妄想。猴子的脸贴着地板,他并没有把它捡起来,鬼先生也无视着路障走近床,说,以前你住的地方窄小,不够安静,那时候你每天晚上都会想方设法找话题,或者倔强地躲进音乐的世界,你被故事包围,你总想着如何开始,如何兴奋地进展,害怕结束,不知道怎么去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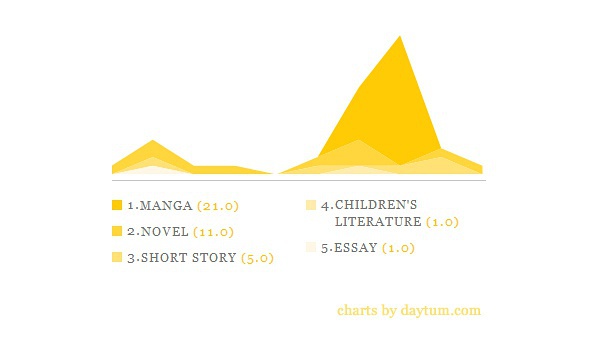
他像接受治疗,卸下沉重的头颅,放在鬼先生的胸口。鬼先生解释故事的框架其实无关紧要,完全可以砍掉首尾,只剩过程来慢慢经营。“无故事的故事,无历史的历史,非虚构的小说,无爱情的恋情,未证实的证据和不确定的确定性……”你看,《……悲惨的宇宙》就是一本参考手册,它是黑夜送来的未知生灵,轻巧地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理论与叙说,人情与狗血,彼岸与此处。鬼先生从未解释过不老容颜的奥秘,他以为那是死亡的封印。静止的时间,静止的样貌,静止的讲述。他一趟趟地搬家,在渐暗的黄昏踩着桌子换灯泡,挂窗帘,假想着未来空间里将要发生的有趣冒险,无性约会,他就嫌时间过得太慢。可是等到那一天,他又会恨时间过得太快。
很正常。把期待当作抵御无聊的利刃,有时会反过来刺伤自己。并不会发生的事,并不会出现的人,在这个世界时隐时现,是你的设想。如果那样,会怎样。鬼先生背着老式挎包,像个少年一样停靠在树旁看书。他睡眼惺忪地点按手机,虚构世界的现实新闻纷杂交错,女巫狼人吸血鬼连环杀手一众狂欢,他在音乐隔绝中走向无所事事。怀念往昔,擦除过去,厌弃自己。鬼先生指责他,为什么把书随身携带却不去翻看。他想说忘了,但说的是没有时间,总被其它事情所吸引。他过了那个阶段。然而,他依旧有种预感,被车撞死,并非幻觉。为什么如此执迷,这种,那种,莫名其妙。他不想解释,无法解释。一旦展开便是灾难。一旦扩写就是诋毁。矫情的朝圣感。他喜欢没有缘由,没有动机,没有起承转合。碎片集合。那本被鬼先生快速翻看的《自杀》,非常像他梦寐以求的遗书,诗与画的拼盘,追忆与重述的共奏。他不痴迷死亡,他不思考存在,他对意义的无意义深信不笃,他是不折不扣的虚无门徒。鬼先生从来不谈死前的故事,对他而言,那不过是面具之前的人生,神秘之谜,毫无兴趣深入。旅行故事讲了很多,提到鬼孩时,他有疑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搞清鬼孩与鬼先生的关系。那是一个十五岁少年,浑身灰白,瘦弱阴郁。
十分嗜睡。鬼先生在公园门口遇见鬼孩。病态感让人好奇又怜悯。鬼先生说鬼孩是停止生长的少年,睡眠仿佛吸去了所有能量。鬼孩走路摇晃,地面随意扭曲,变形,鬼孩一不小心就能沉入对倒世界。没有人能看见[ ]。没有人能伤害[ ]。鬼先生把鬼孩带上了马戏团的旅途。新奇,怪异,都是误读。这里是最终进化少年的聚地。烧死自己,捅死自己,淹死自己,跳死自己,笑死自己,
杀死自己。头破血流,碎裂开花之后,才会有新的出生。鬼孩那些把戏的幕后体验,让他想起曾经做过的一个梦,“兔子优雅地起身,兔子急速地奔跑,兔子缓慢地坠落,兔子漂亮地消失”,他拼凑出梦·想中的鬼孩,身着灰衣,背着老式挎包,停靠在树旁看书,低头隐在背景里。他怀疑R先生不止一个,不论哪一个,他都已不再在乎。R在梦中指出灰衣少年,R说你爱上了故事人物,R在电话里唱了一小时歌,R问三年后你会在哪里,R在半夜发来人设反馈,R说为什么你还没有厌倦,R在评论里虚构了多重身份而你并不是你,R说你好,R不说再见,R有说过模仿你是相互影响的必然,R没有说过不会再有下一次真空消失。
Everybody leaves. Nobody cares.
他听男声凄凄切切。他听鬼先生继续讲鬼孩的奇遇。被陌生人捡回家,像只流浪狗。在拥怀与亲吻中若即若离。最终离开。留下清香印记。无人能缕清去路的脉络,故事在结局的节点告一段落,虚构中的走向持续偏离,最终抵达空无。没有结构没有对话没有高潮没有叙述没有反转没有流动没有
鬼先生撕掉杂志,将男人们贴在墙上。正如墙上的鬼先生一样,定格在奇异的瞬间。他才不会幼稚地去亲吻鬼先生。对他而言,死去的鬼先生是别人每年定期缅怀的男神,而非他的本命。他偶尔会看到屏幕上的鬼先生,与记忆中模样相去甚远,切换不同角色,却永远年轻。他总会想象剧情结束后或者被编剧略去的故事,填充的乐趣与观看并行,在现实延续。鬼先生会说正是这样,你夜里才睡不着。虚拟人物在脑海里存活太久,几乎融入了记忆。他知道那些人物会做出什么举动什么选择,也知道那些人物并不会真的陪他走下去,保持新鲜。像潮水一般来了又退,然而终有一日,他只会觉得名字熟悉,其余印象皆淡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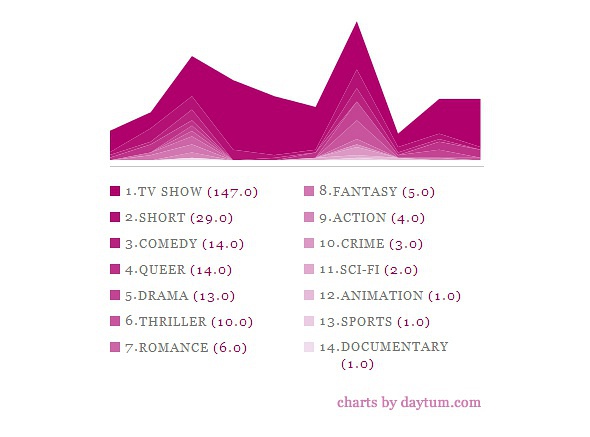
在睡了又睡的夜晚,他一遍遍尝试长呼吸法。眼皮之下的昏沉,后脑之上的活跃。仿佛有无数个自己,因为不同的决定过着不同的生活,在同一时间同一世界的岔口,他观看着他们偶遇、争吵、安抚、背叛,不停假设其中一个他返回到另一时间点做出改变,故事线将会如何发展。不同人的叙述分支,汇聚到同一天同一点,他站在过道,等待电梯下降。
故事向前。
疗养院坐落于城郊,山峦叠嶂,树木重影。他倚靠在午后花园里,摊开一本侦探小说却不关心谁杀了谁,更好奇身边飞来绕去蝴蝶们的游戏轨迹,身影渐长,是刺向时光的暗箭。鬼先生早些年会定期来看他,为他讲解藏于建筑背后的故事,那些修女们在地窖里养了一只怪兽,胃口极大的怪兽每晚要吞噬十三个居客的噩梦。疲劳,病痛,丑陋,贪婪,傲慢,偏执,空虚,一一隐灭。光线再度造访时,居客们身心平静,如前一日,他料想着记忆已然退场,却不知草木茂盛,新花又绽一朵。他慢慢习惯做一个静候日出的居客,鬼先生多年未现身,以为是时候了。直到有一日,他去仓库取花肥时,铁门背后的歌声使他正要开锁的手停顿下来,静静地等歌曲终了,他重新邂逅不一样的鬼先生。
散发禅意的眉目,看淡一切。鬼先生说当年你那么纠结身份,以至轻视任何纠结身份的案例。他说他并不纠结,只是觉得没必要因为厌弃,就兴冲冲站立在铁轨中央。他对自杀者充满敬畏,对死亡之眠充满恐惧。有时会更偏激地故意推迟入睡,看屏幕泛着梦幻,看天色渐入澄澈,他站在窗前洗手,看挨个整齐停靠的彩色盒子在十几秒之后依次消失,他折返床上,诧异正站在阳台的鬼先生,窥视着另一边的生活。
去旅行。太平常。去逃亡。太戏剧。抛弃拥有的一切,重新认识故人,碰巧搭讪凶手。在世界尽头的末路,写最后一篇论文,诚惶诚恐,交给死亡。死亡问他。是怎样度过这个夏天。
绝望。封闭。鲜肉。童颜不老。青春尽可称王。他回荡在男神B的肉麻情话里,相信不真实,相信不般配,不信所有的理智检讨。所有的男神都是别人的男神,他只当作玩笑的一部分,就好像无数次跪求鬼先生的隐身术,不需要回应的反刍行为。层层叠叠幽暗之心。影影绰绰热枕之火。异爱者的终南捷径。一切终好,只缺
夺命卡车一轮轮碾过,喧闹静寂喧嚣死寂,让无声变成更可怕的煎熬。他不知道调整过多少次呼吸和姿势,四小时过去了,夜魔愈发凶猛。半坐起来静候睡意从头顶渗下,虚晃走到窗前,迷蒙视线中只见移动光点。打开窗,户外的冷气才让他觉察到冬寒,关上窗,噪音丝毫没有减弱,他戴上耳塞戴上耳机或者把头压于枕下只会让入睡更艰难。最终,他绝望地放弃了。问鬼先生有何良方。答曰每天十一点睡觉,那年你不也坚持了十天半个月。他心说那还不是因为没有网络,看三小时书比药物更催眠。你需要接受治疗。不。那么重新播放音乐,世界只剩下室内。

鬼先生坐在床头,脱线木偶一般变换着奇怪手势,他躺靠过去,试图看清黑暗中的幻术。面具从额前脱落,鬼先生的酒窝是一潭深渊,星火闪熠。他目睹面孔漂浮,动物旋转,器皿碎裂,月球迁移。他对那幕场景清晰无比。本和丹,缠绵在索拉里斯的爱床上,凝重,严肃,疏离。
另有V先生招一招手,本就从墨尔本跑去雷克雅未克定居,然而,V先生更像是个雇主,开了间卧室,供本与丹随意示爱传情。本/丹二人也不浪费一点时间,合作专辑,为电影、舞蹈剧配乐,在冰寒之地牵着雪犬穿越黑暗,噪音,万籁俱寂。鬼先生说这便是理想生活,你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另一面。他不以为然,他开始习惯断舍离,时日无多,重来一次的机遇太过渺茫。R先生有时会在网络发些家居和爱犬的照片,他无心围观,最后就这么淡去,他总是这么劝说自己。R是万花筒里的小碎片,一个动静便有新的模样。他喃喃自语π的经文,另一个宇宙的空白不可能变身现世的画板。画面拉近。
梦境向下。
他摇摇脑袋,这不是梦。绕到屋后的竹林边,他瞅见骑自行车的少年一闪而过,有些懊恼地追赶,最终沿着小路来到了一所废弃山庄。场景跳切至室内。少年随手把挎包一扔,有些愤怒地质问。为什么跟踪。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别处”。快进8倍。他抱着少年靠在窗台,雨点从底部缝隙轻溅在他的背上,凉意穿行,两手间的炙热随即迸发,温泉,火山口。他轻轻抚摩靠在肩上少年的发,银河银河。电视屏幕映照出另一幅场景,本穿着背心,裸露幽怨,丹身着皮夹克,紧锁冷酷。他等过早晨,中午,傍晚,等到了P的上线。他对P说,梦见了你。P回,今天心情超不好。他从来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转移话题,或沉默聆听。听鬼先生给出吉日上签,听仙雾缭绕的无声舞蹈。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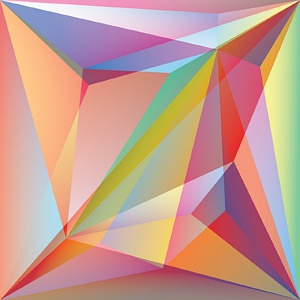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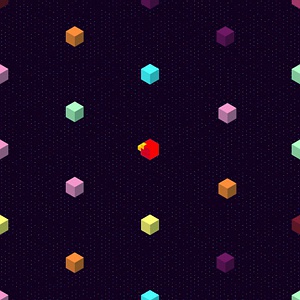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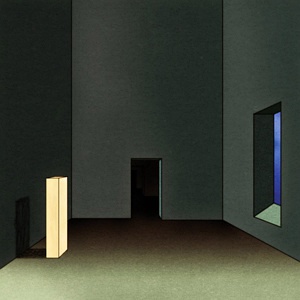 |
|
 |
|
 |
|
 |
鬼先生曾经写过一首歌,献给男孩的最好电子乐。骄傲,满足。他并不理解最好是有多好,每个爱男孩的男孩都爱电子乐,找个插头,即可充电。奇妙物语,不缺表演。鬼先生说,每个月集中创作一首歌,代表十二个方向,并无整体概念关联,只是心情写照。所以你换了十二件衣服,摆了十二个造型,模糊、遮掩之中还要印上专属纹样,是有多讲究。他无视唱法语的鬼先生,爱慕唱英语的鬼先生。这一面貌的鬼先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微妙的色气,在他惊奇的意外发现中,答案浮出画面,以八十年代的同志色情片配乐作为混音灵感的鬼先生到底是虏获了多少淫魔,他不想知道,他想问一个问题,今天你快乐吗,他想说一则故事,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他想拍一段视频,竹林里的隐秘瞬间,他想做一项全新设计,星球上没有死亡,没有睡眠,没有竭尽一生的孤独,没有耗尽心力的冷漠,没有没有,只是
是有多空想。鬼先生说曾经去过拖延镇,那里的人每周只工作一天,日夜无休地赶完前六天的活。人称周一先生的鬼先生跑过去左瞧右看,为那高速缜密的分工合作惊叹不已。经过二十四小时负荷,人们会先睡个长觉,然后便是各种无法自制的游乐。鬼先生说,你无法想象那是多疯狂的景象。他倒觉得这样大起大落在重压与轻松间游弋,是无聊人士追逐有趣的不二选择。慌张,压抑,不知所谓。他关灯开灯,关门开门,关机开机,刺眼屏幕的肉体晃颤,转头侧身,扬手翘腿。欲望向上。

集齐七颗龙珠会唤来。攒全整套卡片会带来。捡掉所有的六面体碎片会发生。他在蔚蓝色梦境不停跳跃。他在血红色房间拼命跳跃。他在四面时钟塔掐着点跳左跳右。他在花屏闪烁的密室随着节拍一起跳跃。他与三百六十度阴森旋转脑袋的猫头鹰擦肩而过。他在四乘以四迷宫中的迷宫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两次闯进8-bit复古黑暗只为确认没有遗漏宝箱。他一次次从高空跳下来,笑看原地重生笑看死亡。他一次次地回到灯塔,找寻熟悉的未知通道,背后是墓地木屋矿井图书馆天文台异次元入口。他想起鬼先生的劝导,月亮影响着万物,等待天空由蓝变至无限透明。睡不着的夜里,他一遍遍掀开被毯,从这边阳台走到那边窗户,隔壁的鼾声清晰可闻,躺回去,爬起来,是沉睡的巨龙。

恶魔城里没有烦人的鸡,啰唆的羊。他向鬼先生索取拥抱,以为这样就能抵挡微寒入侵,骚热来袭。鬼先生开出了借条,那是献上日夜的喘息。他给出保证,做了交易。他享有双重世界。阴阳。生死。面具人生。他在睡不着的午后,召唤出玩具,玩具说这次得换个花样,时间充裕,躺平放松,说出你最想要的,肮脏的许愿。服务,互助,共步阑珊。他放开拥抱,侧过头躲避灯光的监视,该走了,去齿轮树顶寻梦,该走了,去雪山洞深找爱,该走了,这不过是一时冲动二次上瘾
三 人 同 床
鬼先生的木屋已闲置多时,偶有登山游客借来暂住,室内残留着R的天真,熊的调皮,鬼先生的冷静。他想起凉亭里的对谈,在练歌声背景里越来越深入,内心涌动,越来越淡去的面容。他睡了不足五小时,被叫醒被教训被推蹭着上街行走,陌生人流中他发现了故人。别人的生活。他等待寒暄完毕,等待白昼散场。他做了很多事情来满足夜晚。他回味着美好时光来填塞虚无。
浴室里有块瓷砖裂开了,他觉得那无关紧要。他很清楚瓷砖的隐喻,不想提及联想,更不愿翻开表面露出底牌,那丑陋不堪的阴暗与疯狂最好成为他的狱警,尽管门无处不在,尽管流出肌肤的污垢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友好暗示。夜强暴了他。他对之又爱又恨。电影里的幽蓝肌肤,梦幻得吓人,他把幻觉当成故事开端,把幻听当作叙述独白,舔舐着无味,坠身虚构。
她在夜里变身为兔。她在夜里伸展如猴。他在昏暗中起身,星尘飞扬的睡意,是亲密相伴的白噪音。没有人能看见[ ]。没有人能伤害[ ]。对。在幻想中不会[ ]。鬼先生在人群里向他招手,他取下耳机,只听见年少的回音。你可以找出所有的钥匙,所有的提示,你永远不会拥有藏宝图。他闭上眼,想象彻眠的最佳姿势,他如半括号般侧身一躺,列车驶进隧道。黑暗。只是一层薄雾。亲吻过后,自画像背景中的
蓝色在坠下。
爵士乐手们带上乡情演绎着奥斯陆天际,从说唱的振振有词,到念白的寂寂无尽。他回过身看见暗影逼近,说着无关紧要的话,褪去衣物,没有一点迟疑也没有再三
12-14, 01, 2014
词条
你,模糊指代;
他,绝对指代;
R,旅行中的过客;
熊,面具男的情人;
引用,过去的回音;
鬼先生,晚上好。
Today in History
2010 • 过路风景
2008 • 这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