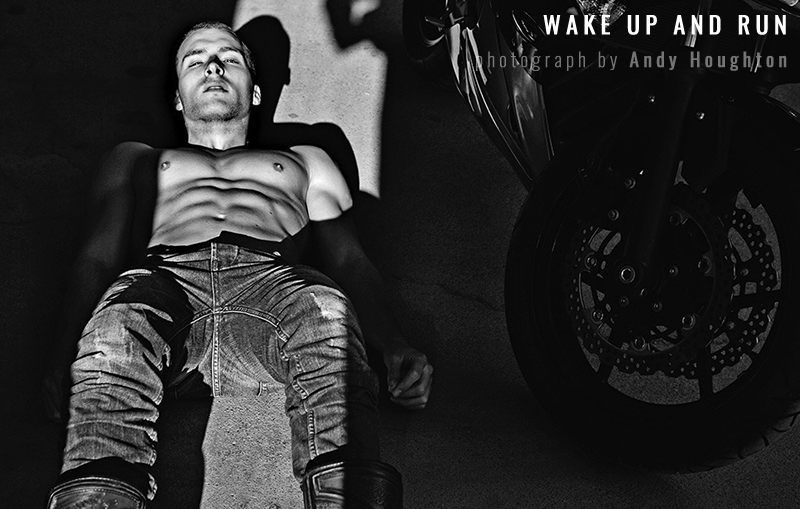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晚上当我进入我睡眠的森林,阴影的眼镜架上了负重的眼睛,以通向眼泪之源的黑暗小径,躲开了微光的荆棘,夜的管束走在了我前面。白天中持续过来的,赶往那纹丝不动的眼睛。”德吉在《门槛》中诉说的旅途,成了男孩麦蒂祷告的坚信;男孩麦蒂祷告的痛楚,成了《大树》里包容的梦想;韦尔贝在《大树》里包容的纷杂,成了鹿眼对照的纯粹;而鹿眼对照的风光,却成了《听说》的神态。
暗火

大火重生后,男孩麦蒂变成了阴阳脸。开场的末世氛围很像雷·布雷德伯利在《华氏451》中所描述的未来世界那般暗无天日,无能为力的路过与无能为力的安抚,麦蒂那半边被烧坏的脸恰似被打上的烙印,也像是联结玄秘世界的隧道入口。但是在麦蒂看来,这更可能是恶魔给出的一种警示,不能拯救自我,但须救助他人。救赎心理越发沉淀,祷告精神也越发坚定。原本懵懂不知晦暗的小麦蒂,因为坦诚,因为信任,误打误撞奔向了流浪。
而喜爱男孩子的名为佩迪格里的教师将自己身上的丑陋与罪恶一股脑儿地挥到麦蒂身上,不住地咒骂,待在牢狱中强抑生理律动与精神折磨。正是教师入狱一事,让麦蒂意识到自己“丑脸”的真实意味,看到了佩迪格里有多么闪耀的纯良之光,当然,是愧疚造成此种扭曲印象,不过对于单纯的麦蒂来说,佩迪格里是好到无以复加的长者,佩迪格里的一切行为皆是出自对孩子的喜爱,麦蒂不太能理解这种“喜爱”,他把它看成是有益的、积极的,于是深更半夜与佩迪格里待在教师宿舍学画地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佩迪格里从一开始就把麦蒂看成丑陋、邪恶的混合体,但没想到自己会亲手把这颗定时炸弹放在身边,引爆自身的罪,还是在半夜。麦蒂把全部罪责都记在心里,如果没有开口,事情会大不一样。在游走异乡时,他反复诵读圣经,章节字句,对照版本,仿佛在审视微不足道的瑕疵。脸上的残疾让他成了丑人,行为的诡异令他变成怪人,不停搭着火柴盒或石头,尝试建造一个可供祭祀的通灵之物,在围观人群的嘲笑与捣乱中却沉默不语。重复此类西西弗斯式的行径,就像重复自责和自我修复。
麦蒂开始记日记,将之当成自己并没有神经错乱的证明。就在内心铺开的字里行间,两位幽灵使者开始涉入,与精神的麦蒂对话,并表明是他们把麦蒂带到他们面前,而非麦蒂叫他们来的。琐碎的日记片段陆续交代出幽灵使者向麦蒂传达的并不确指的使命,而麦蒂也由此明白自己“精神之脸”的损坏才是罪孽的原初。
努力接近一切事物的中心。可是麦蒂并不知道在那中心还有一丛烈火。苏菲和托妮是一对双胞胎,发色一黑一金。苏菲在苦思冥想、想“当然”、“好运解释一切”中长大,出落成美丽的祸害,对她而言,性带来的触动却无关痛痒。在苏菲的潜意识里,有另一个坐在、趴在、躺在、靠在黑暗隧道出口或入口那头的苏菲,好似脑后有另一双眼睛,可以看到本不应看到的角落。意识攒动带来的灵光给予苏菲更多的满足,这种满足比肉体接触要充实,受好运使唤、被黑暗推进,苏菲却像脱线木偶那样,不按常理出牌,言行举止几近逻辑紊乱,没有前因后果,却有野心和目标,苏菲想玩一场大的,不是梦中的虐杀,不是马厩墙上贴的海报宣言,而是将黑暗之火烧上云霄的真实风景秀。
最后这场火的必然,把麦蒂带到了属于他的必然里,再把麦蒂带到了佩迪格里的必然:燃成火孩的麦蒂把双手伸开,伸进紧紧抱着彩球的佩迪格里的双手间,把球从那里带走了。
可怜的佩迪格里连最后也不能得偿所愿。但不可否认,是麦蒂把扎根在佩迪格里身上的执念连根拔起,他解放了他。
《黑暗昭昭》无愧为威廉·戈尔丁最富神学色彩也最“黑暗”的一部作品,Darkness Visible,看得见的,可辨明的,黑暗昭昭。最表层的象征自然是麦蒂那被烧焦的左脸,虽有人工植皮,却仍掩不去那不堪入目的狰狞丑态,这对年幼的麦蒂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而像两位幽灵使者说的“精神之脸有待痊愈”并不那么可靠,因为在小说的内心探索路上,麦蒂的精神之脸早已修复,或者说从未损坏,损坏的是那份单纯的信任。对照外表美丽内心幽暗复杂的苏菲,麦蒂着实可称得上“心里美”了。
深层的黑暗寓意关于人物内心,或者说不确切的人物所代言的不确切的时代下的人性挣扎。小说背景是在二战后,在大量内心涌动的叙说下,客观时间框架早已沦为符号般的存在,却又不置可否地为主体黑暗添油加醋,就像秉烛夜游,冷战、经济萧条、物价上涨、计算机出现……犹如若有若无的盆栽,在道路中央,清晰可见的是来自黑暗的使者。
第一部“麦蒂”,在麦蒂日记处结束,幽灵使者的现身已经是平常事;第二部“苏菲”,衔接着麦蒂撞见双胞胎姐妹开始叙述,到苏菲满怀心计与托妮重逢为止;第三部,“一就是一”,以书店老板西姆·古德柴尔德为视角,观察黑暗使者麦蒂与黑暗受害人佩迪格里的接触,并且搭回对苏菲姐妹童年遐想的那条暧昧线,最后他和曾见证佩迪格里事件的老教师埃德温·贝尔一同沦为犯罪事件下的巧合者。
在第三部出现的麦蒂日记里,简要记述了与佩迪格里交流的失败尝试,在麦蒂的冥想中,第三位白衣幽灵现身了,在之前的红衣幽灵和蓝衣幽灵也在一旁。白衣幽灵令麦蒂敬畏,白衣使者头顶有一圈太阳的光环。而这一位,应是使“黑暗”昭昭的始作俑者,一如“一就是一,孑然一身,更多的事情也将是如此”。
暗虹

以“蚂蚁三部曲”闻名遐迩的贝纳尔·韦尔贝,写起短篇小说来好比清新治愈的睡前故事讲述者。《大树》收录20篇短故事,公车地铁居家旅行必备良品,翻一翻不能令你返老还童也能带来会心一笑。
《大树》更像是作者的灵感断章记录,不考虑铺陈和发展,把那些闪光的、迷人的梗概梳理成餐后甜点。读起来可口,读多了意犹未尽,读完了又觉得短小得太腻、仓促得不够回味一二。毕竟这就是一本灵感、奇想的集合,虽有骨架,血肉却不够丰满,但对于消遣来说,已足够轻松。
有关外来事物的介入,诙谐之余不无讥讽。《天外飞石》令巴黎人忙个不停,却不知这只不过是某一位的投机把戏。《宠物人》列出了外星人对地球人考察研究后的诸多结论,一本正经的语调中所流露出的善意又让人哭笑不得。《青年神仙学院》更像是地球村的军训与演习,有评级与考核,还有更多不在面上的拉帮结派冤冤相报。《梦中情人》是一位女神,然而却可怜到需要登征婚启事了。
有关科技生活的未来或者平行现在,诙谐之余不无寒意。《穿越时空之旅》令人想起那部著名的《回到未来》,但在这里,更像是不廉价且黑心的时空旅行招待所,尤为要注意的是,它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小心轻放》的是一份圣诞礼物,打开礼物的前后,儿子好奇指数略有浮动,父亲耐心指数一路上升,对于喜新厌旧的儿子来说,自制小宇宙能被折腾三天已经是大限了。同名短篇《大树》设想了一棵人性化的智慧之树,它能指引我们走向有益子孙后代的绿色创意未来,但这棵大树要从电脑程序开始,至于这个主意,要待构想者睡一觉再说了算。《飞蛾之歌》顾名思义,是几位有勇有谋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尝试登日。《沉默的朋友》将利欲与谋杀摊开来,也挡不住故事叙述者对那位死去的女性朋友的爱意,而这位朋友苦于无法说话,最后只能在电流刺激下指出令凶手崩溃的物证。《透明人》是研发的一种后果假设,至于《完美世界》则是科技未来的至臻模板。
有关存活于现世中的怪诞现象或臆想,诙谐之余不无无奈。《符号控制》像可以看明事物本质的白日梦,好比说文解字,好比野比用了多啦A梦的道具后就能看到镜中的自己脸上写有“人类,气质平庸,面有倦容,戴眼镜,容易被欺负”的字样。《想独立的左手》几乎是郑渊洁《思想手》的另一版,不过更趋向于“非暴力不合作”。《隔绝》提出与世隔绝的绝妙极致,是灵与肉的彻底分手,是对一切浪费生命的行为的彻底摒弃,大脑所需的养分不多,于是子孙后代像供奉灵位一般供奉起这位超凡脱俗的精神至上主义先驱,先驱却不幸隔绝在绝妙的舔舐中。《最后的反抗》是对日趋老龄化社会的一番极端预知。《生死球赛》把世界杯升级为超级军事对抗赛,可是重要的足球规则依然不变,比如不能用手触球,比如以球入门为得分。《一本书的命运起伏》在对流行读物的调侃中反思着经典作品的寂寥受众群,最后却不忘来一段广告性质的自卖自夸。
在此之外,《暗夜》是纯粹的冥想,古典战争融入个体战争的黑暗中。至于本书的压轴作——《数字迷城》更像是思维悖论下的造物,跟只认识10以下的世界里的人来谈9加9等于18无疑是类似巫术一般的神谕,然而求学好奇永无止尽,少数派一马当先,他们必将成为数字迷城外的先知。
暗夜

一位在“神经衰弱”阴影下迟疑不定的男子,被派遣到一所私立女校任代课教师,书名“鹿男”的所指就已很明显。
美丽的奈良有美丽的鹿,倒霉的男人有倒霉的苦。被研究所的同事说神经衰弱也就罢了,被才认识不到一周的女学生说神经有点脆弱实在是人品问题爱你不是两三天。不过事出有因,谁让你上任第一天就对人家凶。
叫堀田伊都的女生就带来一个巨大的伏笔,甚至在剑道比赛高潮时谜底几乎呼之欲出。原本是“信则有”的奇幻小说,却进展到“到底是谁”的伪推理小说,不得不说是设定的缘故。鹿、鼠、狐狸是守护神器“眼睛”的三位使者,“眼睛”六十年易主一次,其中需要指定人类来传递,名为“送货”。倒霉的教师成了鹿的“送货人”,他需要从狐狸的使者那里拿回“眼睛”,而阴差阳错地,悬在嗓子骨上了却还没拿到真正的“眼睛”,陷在谁是“狐女”、谁是该死的老鼠如此这般的揭面具无奈局面里。而一天天进化为鹿的脸,早已让他欲哭无泪。
《鹿男》对节奏的把握还算努力,在时不时冒出的关于古代纪事的闲扯中亦埋藏着某些推进线索,由浅入深的使命一旦明了后,就变成了主流向的命题。无关乎平凡人物化身英雄来拯救“啊多灾多难的日本”,对于早已经历过“日本沉没”的国度来说,这点源远流长一千八百年的劫难镇压算不上什么,而对于只是来奈良放松心情的可怜男人,责任重大加上鹿男进化的恐慌已经不是逃一逃就了事的境地。
于是又带出一个永恒不息的话题,人与自然的和谐指数。在鹿那淡悠悠的话语里,人类对问题推卸责任早已家常便饭,而像它们这样的管得宽动物对维护某些人类自己都忽视了的问题反倒乐此不疲。怎么样,事到临头桥不直就又想逃了?
神经衰弱的男人没什么本事,死要面子而已。
晚成名的作者在序言里的一番自白,没什么看头,小时候爱幻想而已。小说正文也说明爱幻想的作者现在也没长大而已。当然这对幻想小说家来讲未尝不是好事。七岁时能听见小人国的鼓笛声,之后就再也听不见,就好比西方国家的孩子长大后便听不见圣诞老人拜访时的铃铛响一样。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是未经世事的孩童纯洁得像那片黑夜,雌鹿一跃而起,漂亮灵动带来神光初绽。
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把梦做得这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还照样落入窠臼把睡美人当成万能解药这般纯情万分先抑后扬还仍然流于平淡让苦情女变成相伴路人。
说实话,在这本小书里见到久违的十二生肖来历传说真有点说不出来的意味,太根深蒂固的东西反而经不起炫耀,大抵如此。
暗星

米歇尔·德吉的诗作晦涩到一定境界了。而问我我也不知的骄傲姿态让他独步法国文坛一晃数年,当然,精华化小众性的路子得不到更多人的赏识也在常理。
如今这本定价不菲的《听说》选录了德吉六部诗集的作品。入选篇目最多的《听说》大多是寥寥几行的无题短诗,“这是在我们之间/手之间的空气招呼/而手在招呼之间/而招呼纯粹的间隔/无与无玩着/彼此送出美丽的显现”,意象简单,没有花俏的辞藻是德吉诗作的特点,但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跳跃、指向断裂使得整体艰涩程度就如同在半空中跳着忽隐忽现的木桩,除了立足之处,一片漆黑,落点总出乎你的预料,令人费解的终点始终不肯到来,而黑暗把你吞尽后,带来空无的视野,除了白茫再无他物。没有焦点没有方向没有结果。
出自《半岛诗歌》的《门槛》把大地比作“很大的遗迹”,“发掘它看守的源泉,缺席凝固其中的重大痕迹。希望有一个国度在等着你,这一写作的爱便是它的出生证。”要迈进德吉诗作的门槛,代价之高毋庸置疑,他的作品是现世的遗迹,过去的流光凝在其中只是一些点缀,更多来自神话时代的表征让一座座遗迹散发着幽静的星光,对记忆、爱与死亡恒久的追寻也令入口变得隐秘微小难以发现,迂回的结构更使它们更像是留给未来人以观赏而不求甚解的来自遥远过去的美妙装饰物。作为与德吉同时代的人们,欲求参透,其实是很无奈的,“一位诗人所做的/另一位诗人无法拆解”。
《文献》仅选收了六篇,却无疑是这本《听说》的精华。《诗艺》是释义与批评的佳作,充溢着各种笑说与文字游戏,无奈翻译并不能将法语韵律同一转换,只能借着脚注,在“狼与狗之间”在“黄昏”之间在“狗与黄昏之间”在“黑夜边缘的狼”之间,兀自想象着那一天色那一呼啸风色。在戏说之外,德吉也不忘一本正经地搞起文艺批评,从字谜、名称与物、作品、读者、现象、故事、日常、平衡、梦幻、回忆、语法、整体音调逐一掠过,而诗歌本身就像“以其精工细作的静谧的开放,开始了有节奏的节庆”,《诗艺》不仅是“释义”,也是找回或者说一次次返回极具“诗意”的“失忆”部分,至于读者读过后的“失意”,德吉大不在意地给了句安慰,“它(诗歌)在自身中盲目地开放它”——我们这些盲目者又何必急于靠近,靠近事物的中心,也许就在靠近虚无,那时意义早已不复存在。
观看德吉的诗歌,确是在雾里看花。或者,是在做一次次短暂又跳跃往复、不无惊喜的旅行。《旅行》像是对《诗艺》的追述,于后段升华为灵/肉对缪斯的赞叹与追逐。神话意象如星密布,自嘲解说穿插显现。回应《诗艺》,“意义的要点,我打开他们的手:把一切放在这里,然后走开……”,一切诗歌一切梦想一切事物,“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地偏远”,因为太过靠近太过解析反而不能看清事物真实形态与本质?“而处在中间的人,被万物模仿,被监视的监视者,他跟他的语言调解得那么好,致使万物都复归其位,同类都相聚成群……”所以看吧,德吉的骄傲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啊。
读者于他,是监视他不成反而被他监视过分的可怜人。过度饮酒伤身,过度兴奋伤脑,过度阐释又伤身又伤脑。对待德吉的诗,偶尔看看当作意外度假或者闲暇时玩的魔盒比较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