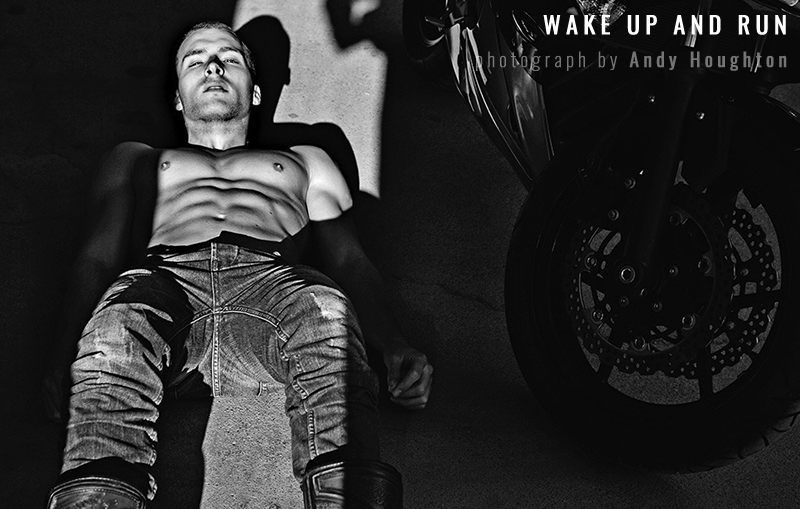二〇〇八年最让人期待的书——除开《跳房子》,便是这本了,《万有引力之虹》。托马斯·品钦的最新作品《Against The Day》是不是又要拖个五年,然后沦入《芬尼根守灵夜》(詹姆斯·乔伊斯)的不可翻境地?不是的,《芬尼根守灵夜》那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管怎么说,让人翘首企盼的品钦最难翻译的《万有引力之虹》总算有中译本,暂且撇开翻译的某些bug,我们还是应对误了博士荒了职称辛苦三年整的译者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唔。
我是广告商的小走狗。
《万有引力之虹》,托马斯·品钦作品,张文宇译,译林出版社,约六月上市。
以下来自译文论坛张文宇先生的帖子:
现选开始部分的一些段落,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部题记:
“大自然不解生死,只解沧桑。我学到的全部科学知识,包括不断学得的新知,都使我坚信:我们死后有灵。”
小说的开头是一阵尖啸声:
“尖啸声划破了夜空。这种尖啸以前也有过,但这回却声势空前。”
紧接着品钦极富张力的语言便展示在我们面前:
“黑暗中,他坐在棉绒座位上。没有烟抽。能感觉到远远近近的金属在摩擦、碰撞,蒸汽噗噗喷出,车框在颤动。空气中有一种强作的镇定,一种惴惴不安。人们挤在周围,混杂于救援物资间——他们都是既背运又背时的下等人、弱者,有醉汉,有对二十年前作废的军规仍心存余悸的退伍老兵,有本城装束的妓女,有流浪汉,还有那些疲惫的妇女,带着很多孩子,多得令人怀疑其来历。”
接着品钦的神秘怪诞也登场了:
“人群在仓库般笔直便利的过道里走着,没人说话,没人咳嗽……他们移动的痕迹融入周围天鹅绒般黝黑、光滑的壁面,陈旧的木材、冰冷的墙壁涂层,混合着那些侧房发出的气味——这些房子偏僻久旷,如今又打开来接纳逃亡者了。就是在这里,老鼠们一个个香消玉殒,只留下魂魄,执着、显眼地贴附在墙体之中,壁画般一动不动……。”
再来看看他的犀利:“别忘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可以自行运作,可以让外行去管。战争中大量死人,这个特点好处很多。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最难能可贵的是,大规模的死亡会刺激那些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小人物,使他们也想趁这些人还没吞完那张大饼时抢它一块。战争其实是市场的福地。被专业人士小心翼翼地称为‘黑道’的器官市场四处涌现。美币、英币、德国马克在消了毒的大理石金库里不停地流动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像跳古典芭蕾。可是在这里,在民间,却造就了一些更真实可感的货币。因此,香烟、性、黑人可以交易,犹太人也可以交易,身体的每一块都可以交易。犹太人也有罪,将来也可能搞敲诈,这个理由对专业人士当然是有利的。”
他的深刻:
“真正的神都是集破立于一身的……上帝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既是阳光又是黑夜,是一切相反之物的集合,包括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
“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别人为你而死。从来如此。什么东西才有足够的价值让一个人为之献身呢?千百年来,宗教在这方面一直独占鳌头。宗教总是关乎死亡的。宗教的用途与其说是鸦片,不如说是技巧,使人们为一套特定信仰而死的技巧。这当然是歪门邪道,可你是谁呀,有什么权利下结论?宗教在过去有效用的时候,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后来,为死亡而死已经不再可能,于是便有了替代宗教的世俗版本——你们的版本。为推动历史实现其预定模式而死。死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死将使历史朝良好的结局靠近一点。革命式自杀,好极了。不过你想想,既然历史的改变不可避免,那为什么不能别死呢?……既然注定要发生,死不死又有什么关系?”
他夹杂苦涩、颓败等反面意蕴的优美:
“那个刚刚死去的少年,拥抱着自己的‘悲伤’,自己最后的牵挂,竟永远把姑娘阳世的抚爱抛却在生死界上,孤单地上了山,终极的孤单。他一步步登上了‘原苦’之山,头上的星群非常之陌生……”
“斯洛索普成长的时期,正值企业接连破产,衰败荒凉达到了顶点。那些神神秘秘的纽约富客们的庄园树篱重又归于绿野蓬蒿,房子的玻璃窗破碎无遗。哈里曼和惠特尼两家搬走了。草坪变得干枯。秋天来临时,远处不再有人跳狐步舞,也不再有豪华轿车和灯火,熟悉的蟋蟀、苹果又成了这里的主人。早霜送走了蜂雀,东风吹寒、秋雨潇潇:冬天必然会来临。”
他行文的特异奇趣:
“罗氏一家有戴发罩的习惯,还喜欢在屋顶上种养药用植物……个别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在饱受霜打雾浸后竟活了下来,其他同类则化作一片片独特的生物碱,归于屋顶的泥土。一同归去的还有那些‘三重’肥料:一是斯罗思朴子嗣们关在那里的优种西撒克斯鞍形母猪的粪便,二是后来的房客移栽的风景树上落下的叶子,再就是这个那个挑嘴的人扔在那里或吐在那里的粗食败饭。到后来,这些东西被岁月的刀笔雕涂得浑然一体,成了几呎厚的土壤画板,表层的黑土肥力卓绝,种什么长什么,种香蕉更是不在话下。……海盗的香蕉早餐已经名闻遐迩了。英格兰各地的餐友们纷至沓来,就连那些对香蕉过敏甚至讨厌的人也来了,他们想一睹细菌们的管理机制,看看土壤如何把那些化学的环环链链缀成眼格小得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大网……”
他的细腻:
“斯洛索普的桌子则乱得一塌糊涂,1942年以来就没再见过木桌面的真容,各色东西掉落在上面,变得层层叠叠。其中有橡皮擦上掉下的千千万万红色或棕色弧形小卷儿,有削铅笔的皮屑儿,有干掉的茶渍或咖啡渍,有食糖和鲜奶的痕迹,有大量的烟灰,有打字机色带上飞过来粘上的细屑,还有分解了的厚浆糊和碾成粉末的阿斯匹林。这些东西形成的官场阴垢一层层渗透下去,顽强地直抵桌面,成为桌垢的主要成份。还有四处散布的回形针、芝宝火石、橡皮圈、钉书针、烟头、揉皱的烟盒、散落的火柴、大头针、钢笔尖、各种颜色的铅笔头(包括不易弄到的淡紫色和生褐色铅笔头)、木咖啡匙、妈妈南琳从马萨诸塞远道寄来的‘萨尔’红榆润喉片、胶带碎片、绳头、粉笔渣……这些东西上面,又堆了一层被遗忘的备忘录、软皮供应证、电话号码、没回的信、破损的复写纸、‘克来姆尔’生发油的空瓶,加上一些笔迹潦草的尤克里里伴奏和弦谱,有十来首歌,包括《面团儿兵约翰尼找到爱尔兰玫瑰》。……再就是一些智力拼图玩具残块,上面画着威玛狗琥珀色左眼的局部、长袍的绿色天鹅绒褶边、远处的叶脉状石板蓝云朵、炸弹(也许是落日)的橙黄色光环、空中堡垒表面的铆钉、噘嘴美女的粉红色大腿内侧……再还有几份军情处来的每周军情摘要,一根绷断的、卷曲成螺旋状的尤克里里琴弦,装有各色星星贴贴纸的盒子,手电筒碎片,‘块金’牌鞋油罐盖子(斯洛索普经常把盖子的铜面当镜子,照出的脸虽然模糊不清,却看了又看),从下面大厅里的交换站图书馆借来的一些参考书:一部科技德语词典,一本外交部发的《特别手册》或《市镇规划》,一般情况下随便什么地方还会有一份没有被卡掉或扔掉的《世界新闻》——斯洛索普是个勤读的人。”
他的文字游戏:
“‘是哪个煤气总管,’一个拿着便当的女人正好路过……/‘不对,是德国霉气导弹,’她的朋友道……”
“他们没有繁荣起来……他们仅仅繁衍了下来……”
“她本来想叫‘真帅飞贼!真帅飞贼!’,可是因为不会发元音变音,说出来就成了‘直升飞机!直升飞机!’”
“据说他的呼噜声足以把双层窗震得啪啪作响,把百叶窗震得摇摇晃晃,把吊灯震得叮叮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