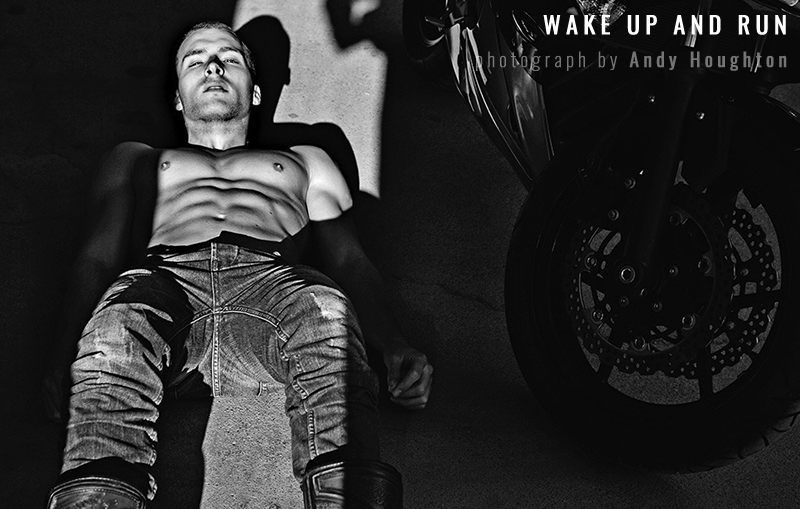头发已开始苍白的阿尔莫多瓦,迷恋上了细语的润泽。宁静却又绝望。
而立之年的罗伯特·施奈德尔,倾情于对睡眠的谋杀。静默而又枯竭。
我开始不知道要如何说起她,柳美里。或许在以前这样的一本书是不会吸引我的眼睛的。或许太过美丽了。
把她从畅销书作家拉回来的决定性的一眼,是自己细细捧着《女学生之友》把四个中篇一一看下。然后就中了她的毒。心甘而不悔。那四个风格迥异,有着四个不同叙述元素的框架,宛若四个不同的作者写的。丝毫也不能与这个美丽女子联系起来。
从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一翻便是被《瓷砖》给深深吸引住。而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是所看过的对人心刻画最深的一个中篇了。
一男子对存在的困惑。其自身性无能的压抑。还有婚变的孤独。却意外在一个女作家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想接近这个女子的心。看她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仿佛有了陪伴的感觉。可后来,在一些事变之后,与女作家见面了。却越说越深入了灵魂。最终无形的力量,让男子杀了她。把她埋在自己铺的瓷砖之下。
我就如此想看着柳美里完整瓷砖铺成后的纹案会有多绚美。
后来,发现《口红》也是她的作品。
几天后拿到书后,搁下了手头正看到2/3的郁闷冷清的《舞!舞!舞!》。在没有音乐的一夜与一下午,花两口气看完了。
是一贯喜欢的南海出版公司的版本。纸页轻盈,鹅黄。
开始第一章,便觉得恰是一个完美的圆形结构。主人公里彩在第8页登场。我倒以为男孩圭是男主角呢。以他为焦距叙述的白蝴蝶的意象在行段间满满的。后来也是以他作结。全然具备了短篇的枝干。
里彩的独特。被柳美里镂进了字骨子里,仿佛就那么天然。淡素。
无法想象一个不到21岁的女孩。毫无接触男孩的经验。不了解自己的三围。不喜欢化妆。不喜欢社会的繁复交际。
而甚至出奇的是,她会心血来潮地只因照片上的美好印象,便花短暂的一天飞到冲绳找一个方圆仅50米大的小岛来度假,而且还美其名曰“沙岛”。
但就这样地表露自我。才是她的社会标签。
记得到后来,黑川慎吾的登场。被描述他的介绍逗笑了。
28岁。1.62米。有必要介绍得这么详细么。但还是无法形成他的英俊形象呀。可是仅知道他很黑就是。
就像他们的淡然的相遇。里彩与黑川的感情真的莫名的沉静。没有说爱。没有说缠绵的话。没有情人间浓烈的氛围。就那么处着。就那么和谐地在一起。似乎谁也分不开。但又没有恪守的约定。
他觉得她很特别。她觉得他很贴心。仅此而已。
这会是有距离的迷恋吧。
要是说到不可少的孝之。那话题便会在我嘴里沉重起来。
这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三角关系吧。而我就一点一点地看着柳美里破坏掉了这个世界的球。于是勉强也想做几个假想完美的球来弥补旋转。
出路的选择与背叛。都是不可掌控的。只能是假设的模式在自己的梦中做做罢了。
真的当一个男人同时爱上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对方都同样爱他。那么双重的幸福也就等价与双重的劫难。细微间便可堕入虚无。
不习惯看这样的爱情。还是幻想着能有性别上无边地超越。但超越到没有尽头,我也就忘记了中心。于是,三人间关系也没有了同心感。但又更无措地痛苦。
我已然想象不下去了。空城里没有爱情。
对她说。对他说。
假如,你是一个同时爱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男子,他们也同样爱你。你该怎么办。又最希望怎样的结局。
橘子说好难选。我不知呀。可后来她想身处小说的话,还是选初恋的那个,而活在生活中的她却无法修改一切。
以前就在一个夜晚向矗矗提起过,而他是做为那个爱着这个男子的另一位男人的角色,即说的坏一点就是女孩的情敌,他倒天真地说出童话故事,女孩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祝福着这两个人的幸福,后来,这两个男子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那天,我差点要说他自以为他是什么“公主”啊!
在深夜,LunaSea发来短信说:哈,能同时拥有么?
我立马骂这哥哥贪心。
然后他老老实实地选择继续独处吧,对谁都公平,睡觉也塌实。而我也觉得这就是低调又不失风雅的作风。可这样平淡下去似乎有点对不起爱恋中的三人。
而LunaSea哥哥接着说,如果是我,无论我如何努力,都不会逃脱人两空的结局,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走出迷局。
而这倒是对那当事者心境最恰如其分的描述。然后已然困在了迷宫里,又如何走出,这才成为了心力的掌控所向。其实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努力与觉醒是重要的。可就是关键不会在适当的时刻苏醒。
对黑川似乎没有过多的好感。倒是很喜欢孝之的个性。而他描述的乌托邦性质的三人生活,也是吻合我心里那股狂想的情愫。那样下去,是童话的“从前”和“以后”,总是那么永远地挂在嘴边。幸福出现在结尾,又延续到永恒。
然后,童话流传下去。
可是这是成人的叙说。于是,事实上你无法找到另外的两个人。哪怕你竭尽全力。
或许,这才是幸福。因为你得总在真实中喘气。
想起阿尔莫多瓦的《对她说》,很感兴趣。却一直没机会看。有个接近疯狂的男子一直在对沉睡的她说。一直在说。对她说。
哪怕自己对着死亡说。哪怕是幻影的言语来回应自己。他也坚持说。
而似乎这就是对深陷其中无法挽回的爱的痴狂作为。若真正存在与里彩他们之中,谁可以平静而真诚不带一点私心地对她(他)说,说一直的心里话呢。不断吐言。直至自己灵魂坠下。
那时,相互总该有一个人会澄净地看看他们脚下的池。泪,是不是落尽,落无声了。
而罗伯特·施奈德尔的《睡眠兄弟》在清醒与次清醒间,歌咏的三人关系又全然简洁明晰。
彼得→埃利亚斯→伊尔斯贝特。一个接一个不错乱地爱着一个。
但全是单向爱情指向,却也痛苦不已。同样是纯精神化的同性恋。彼得时刻没有放弃对埃利亚斯的注视,尽管他听不懂那钝化的轻语,彼得还是对他说着。跟到山林。跟到石溪。跟到不睡的麻痹癫狂。
即便他死了。彼得还是对着有情人刻字“E”的树干说着。思念不绝。
而单纯执著化的埃利亚斯对一生喜爱的情人的说话,凝结到了歌声悠扬的音乐中去。近乎死亡的华美。
就算没有出路。你也要对爱情说话。不断。不老。更不能哭。
或许我们更习惯寂寞。正因为说给了寂寞听者。于是才没有了回响。梦想,与无梦,都在无言中轮转几世几生。
他她没听到。那时我和爱情早已走过最后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