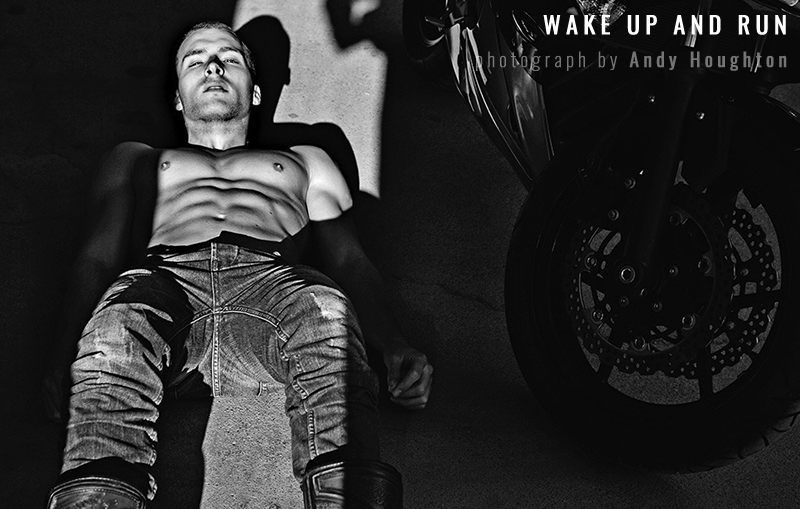photograph by Francois Burgun
我相信遗忘是件美妙的事。今天,就在人群中找熟悉的面孔。原来是你。
——他有异装癖,经常用裙子当围巾。他很瘦弱。他打一个喷嚏,熊先生就会马上过来,探出舌头,温柔地舔他的嘴角。熊先生在阳光强烈的时候会隐没在白墙里。他很生气,只要找不到熊先生就会把东西乱扔。有一次,就把汤勺甩向花瓶。那束百合,有微卷的花瓣,在地板上彻底裂开,就好像他咬破的嘴唇一般。
无论是谁来,都是一样的流程。我在昏暗的公车上,对香水感到恶心。
——熊先生总是很好脾气地低头,说,“我带你去洗洗吧。”他把面具重新戴正,装样子的咳嗽,抓住熊先生的手,然后将其带入浴室。他仿佛要溶化在池中。熊先生流下口水,同样被洗浴的水同化,但是他眯着眼睛,就要取下熊先生的头罩。真该死的,你是骗子。你是骗子。
我在等一本书的到来。一部口头的神话,一份黑暗报告书。他说,正为你送过来呢。
——他躺在床上。毫无特色的白衬衣。几条领带。花色。他知道自己选择的是灰蓝色。那些带花的都是熊先生给系上的。歪着头,斜着眼,他知道真相。但不只一个。
回去吧。回去吧。
——熊先生是男的。他当初让熊先生进来,是因为他需要园丁兼清洁工。不过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他就开始命令熊先生为另一种身份。比如说,可以骑着走的熊先生,可以练习拳击的熊先生,可以用来睡觉的抱枕熊先生。熊先生很乐意为他做任何事,没有哪件失败过。在一个夜晚,三点钟的样子,他醒来,光着身子爬起来,双手扶着床,同时在左右寻找着熊先生。那时候,熊先生的头罩已经放在地上了。他的阴茎向上硬挺,抓住熊先生的耳朵,便将熊先生的头拉近他的胯下。他就要崩溃的那刻,电话来向他问候。汗水从他光亮的肩胛骨流下。熊先生已经咬住了他的乳头。
“你还不走!我要用电脑。”
——熊先生是女的。自称为先生,是想让自己这份工作做得更好。他总是不屑熊先生的手脚,好像一个蹩脚的机器人,虽然对主人忠心耿耿,可是却又不自觉地偷懒。熊先生最初来的时候,是要改进他的生活,因为他日渐消瘦。但是他毫不在意。熊先生时常劝说,你就不爱你自己吗?他会每晚牵着熊先生在房间走一圈,然后在地下室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模型,每当他在前面走的时候,熊先生都会很自然地贴在他背上,生怕他会消失一样地触摸他。后来,当他借用熊先生的身体来发泄时,就发觉熊先生哭起来的时候是夜晚最美的时段。他透过面具呼吸,只有舌头可以感知熊先生乳房的味道。某次,熊先生对他说,我喜欢你的眼睛,你幽灵一般的双眼只有在此刻看着我。
我站在他身后。
——熊先生是幽灵。是他还没依靠面具生活之前所杀死的邻居。熊先生是他为女儿买的布娃娃。因为女儿不小心溺死在浴缸里,所以熊先生始终开口闭口说,“我帮你去洗洗吧。”熊先生是他梦中的谋杀者。跳出来,不再追杀他,但是囚禁着他。熊先生是他正在创作的一个主角。他想依赖熊先生来换取名声,哪怕不惜牺牲隐私。
他有点生闷气地去上厕所。
——熊先生是他的厚棉袄。他习惯了裸睡,但是也有踢被子的坏习惯。一般凌晨六点之后,熊先生会把厚毛毯收回身上,然后离开他的床。在客厅等候着他第一声命令。只是,上午八点钟之后,熊先生已经躲在白墙里。他每天起来都会发一通脾气。待到下午阳光微弱的时候,熊先生总会低着头爬出墙。在洗衣机旁等他骑上来。两只手拽着熊先生的耳朵,双脚蹭地,头微向后倾,他获得一天里第一份快感。于是,他弯下身,拍打熊先生的面庞,说,你真乖,你说你要什么惩罚呢?
我坐下来,把粉红色的封面摆在桌上。然后翻为封底。
——他将围裙系在熊先生的双肘处。他说,我们去厨房吧。
卡夫卡被村上春树怀念,那个叫乌鸦的少年。我想念他们,这些叫珊瑚的少年。
——做爱之前,熊先生总会取下头罩,这时候他获得第一个吻。他坐在熊先生身上,对准了熊先生的心脏,下力一捶。他说,你会和我一起死。熊先生微笑着看他,他取下面具,骷髅一般的头颅轻轻地靠在熊先生的颈下。
他们祝我深夜平安。幽灵在你身后。
[ 2006年平安夜 ]
附记:终于买下The Coral的第三张专辑Nightfreak and the Sons of Becker。粉红色的梦境。神秘的面具男与隐在树枝后的熊。作为一个收集狂,他们的四份作品是一份完整的成长报告书,我有幸聆听。这些叫珊瑚的少年们,制作了这个粉红色的梦,我拿着它,准备度过我的平安夜。另外,一直念叨的《美国众神》终于拿在手里,触感不错。以上,是一份行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