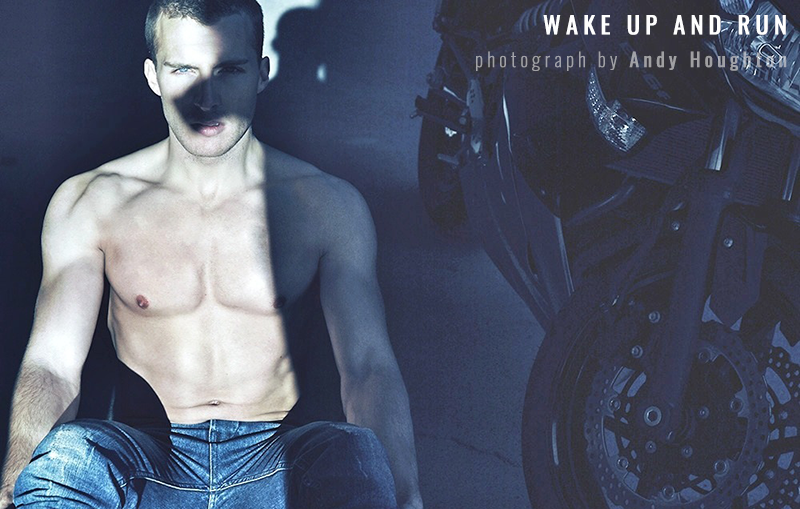“短经典”系列刚出来的时候因其独特的选题和丰富的封面配色而迅速获取了一批文艺青年的关注,两三年时间陆陆续续出版了27册来自世界各地优秀作家的短篇小说佳作。突然间,“短经典”换了家出版社,结束了色彩封面,换成与塞林格系列三本同样的素底横条封面,当然两份设计都来自张志全工作室,只是太没创意了一点。新封面显得更严肃正式,也更低调,或许是为了这重新开始,就连系列编号也从头开始,第一辑共10册,包括多克托罗的《幸福国的故事》、宫本辉的《幻之光》、维尔高的《海之沉默》、卡萨雷斯的《俄罗斯套娃》等来自八国的作品。
也许网友戏谑成真,“中经典”也已问世,就等“长经典”的现身。至于信誓旦旦要一直做下去,至少推出一百本两百本世界各地重要作家的重要短篇小说的“短经典”到底会持续多久,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时光记忆

安东尼奥·塔布齐是继卡尔维诺之后意大利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优雅、清淡,蕴含着浓郁诗意。《时光匆匆老去》更是作家离世前的一份时光告慰书,“这些故事实际上都存在过。我只是聆听故事,并以我的方式叙述出来。”
是的,9则故事都有出处,分别献给不同的人,塔布齐抽取了上世纪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瞬间,却将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细腻转化为与时光拉锯的个人故事。献给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将军之间》再次重申了一个论述,历史比我们伟大,生活也并非对艺术模仿,现实总是超越想象。是真是假,还是被时光洗练过后残存的一点记忆,故事里的人物像被摆布的棋子,他们在讲述者的版本里规规矩矩地走步,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抗争。讲述中的讲述,这一嵌套关系也使得故事变得遥远而朦胧,更不像真实事件。塔布齐并没有以多么感性的口吻来加强时光流逝的痕迹,反而是以十分克制、审慎的笔法将时光悄无声息的渗透铺陈得无处不在,如沙漏一般从始至终地坠下。
《圆圈儿》是环绕自身的马群,是记忆,是思绪,也是时光。《淅沥,淅拉,淅沥,淅拉》是疼痛发声,是死亡脚步,也是幼时“假设游戏”的来回套问,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所能带来的美好乐音。《我眷恋风》是女人,是诀别,是情歌,是每一个不可再来的邂逅。《电影节》是善意谎言所能达成的最大成就,也是光影间最激动人心的寂静现实。
而最触人心弦的莫过于那篇《云彩》里的对谈,二战老兵与十三岁少女关于语言、战争、历史的闲聊充满了时光感,敬畏与唏嘘些微显现,话题衍变又如天边云彩那般变幻莫测,士兵重游故地的目的不为缅怀,只是为了观察可预测的云彩,少女努力与士兵交谈,顺而也带出自己一部分不安的过去。可是,在已逝面前,任何讲述都显得无比苍白,塔布齐并没有过分铺开时光的跨度,他只选取瞬间,只讲述往事,简练,隽永,是时光匆匆老去的遗痕。
真实人性

非洲作家强手如云,令人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尼日利亚)、南丁·戈迪默(南非)在中国的译作陆续也出了一些,而被誉为尼日利亚传奇作家的钦努阿·阿契贝这两年开始小热。被选入“短经典”的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同样来自尼日利亚,她之前的长篇小说《半轮黄日》获2007年奥兰治小说奖,史诗般挖掘出20世纪60年代的尼日利亚在内战背景下的残酷真实。
延续着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她的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继续加强着身为女性作家的思考与自觉,并与时俱进地将视野扩大为尼日利亚、美国两国来回穿梭的文化差异,并埋入深层次的乡愁。她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角,强烈的性别叙事极具感染力。如《赝品》里迁至美国的妻子默默忍受着丈夫远在尼日利亚经商的寂寞,意外听闻丈夫外遇之后,她干脆地剪短头发,并在与丈夫的碰面中不动声色地作出了扭转现状的决定,这是何等冷静与坚强的定力。再如《个人感受》中在宗教冲突乱战中两个躲在商店避难的陌生女人因为不可抗力而互相交流过往历史,她们等待,她们安抚,死亡在户外的当下以及穿插其中的未来时隐时现,这段躲避成为了未来回想的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断片。
追寻美国梦,仿佛成了阿迪契笔下人物最常见的梦想。无论是《赝品》中为了过上更好生活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还是《美国大使馆》出于政治避难而被迫申请逃往美国的知识分子,美国成为了平静、自由、富有的梦想之地。当然了,相对动乱的尼日利亚来说,美国明显好太多。《绕颈之物》这一篇就是从尼日利亚延伸至美国的追逐之梦的生动写照,被签证抽奖抽中的“你”来到了美国,住进了称之为“叔叔”的家里,在学习与侵犯的抗争中“你”选择了出逃,在不知道身处哪儿的时刻,“你”选择做一个透明人,每当夜晚降临时,黑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缠绕着“你”的脖子,让你窒息难耐。而当“你”偶遇爱情时,“你”并不知道那种感觉就叫爱,黑夜中的绕颈之物明显减少了缠绕,更奇怪的莫过于那位男友身为白人却对非洲及其文化十分痴迷,这让“你”觉得诧异,这段看似不正常的关系带给“你”的美好难以言说,可惜一切终有结束的时候,“你”哭泣,在他拥抱中离开这个曾是梦也已带来梦的国度。是否归来,那不是故事的结局。
尽管很多故事发生在美国,但阿迪契的聚焦点始终在海那边的尼日利亚,美国仿佛仅仅是个装饰背景,用来强调文化冲突和烘托思乡情绪。《颤抖》正是如此,两个因为坠机事件被迫一起祷告的尼日利亚人开始一点一滴地交涉彼此的过去,那片遥远国度上发生的事仿佛只在记忆和照片里,他和她在忧愁的记忆回溯中不停提到上帝和信仰,这或许是支撑彼此继续前进的最大能量。随后的《婚事》更强调着两国文化差异,在反复纠正妻子的用词背后隐藏着丈夫爱慕脸面的虚心,然而,为了过上更富裕的生活需要历经相当勤俭的当下,妻子从无所事事到争取工作自由,竟还无意间获取婚配丈夫的惊人过去,可是她有什么选择,她在这里举目无亲,除了回到那个家再也无处可去,至少要待到她有工作签证能自给自足才行。被男性支配的女性现状,让人备感无奈,在《猴跳山》的非洲作家集会中同样如此,可是嵌套其中的作品片段却不这么认为,最后的发声没有让沉默继续沉默下去,而是骄傲地选择了拒绝和离去。
阿迪契讲故事的方式十分亲切,就像第一篇《一号牢房》那样循序渐进,从一开始吸引读者到最后带动读者与讲述产生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刨去社会冲突、信仰坚持、文化符号,流淌在她笔下的始终是人性真实。
怪诞日常

薄薄一本一百来页的小书,却蕴含着极大的张力。阿根廷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以14则短小精悍的故事告诉人们,何为大胆的想象力、大胆的意象以及让人无法预料的突转和结局,悬念从一开场便提在嗓子眼,促使人们聚精会神地阅读每一字每一句,紧张和流畅是短篇小说不可多得的两大法宝。
玩弄动物的意象,仿佛是这片南美大陆的文学传统,“短经典”之前也出过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动物们的象征带来光怪陆离的梦境故事,既是脱离日常的荒诞,也是充斥日常的神秘。动物意象的援引,很容易带来魔幻色彩,在短篇小说有限篇幅中则更具戏剧效果。《杀死一条狗》中,狗成了可怜的受害者,它们在广场漫行、瞌睡,却被迫卷入一场无稽的组织考验,一位中年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杀死一条狗”的条件以证明自己的冷酷决绝,而负责监督他的人名叫“鼹鼠”,这几乎又是另一层动物世界优胜劣汰的隐喻。《蝴蝶》看似美好,却也只有短暂的美好,一位父亲站在学校门口对同伴夸夸其谈女儿的穿着是多么美妙,在等待之中,一只蝴蝶停靠在肩上,他本想捉住这只蝴蝶讨女儿欢心,却不小心弄断了它的翅膀,在同伴的建议下一脚踩死让其解脱无法飞翔的痛苦,可就在那时,一群蝴蝶从校门口涌出来,花色各异让他一时害怕难以找到与脚下蝴蝶花色相似的女儿。蝴蝶,从真实到虚幻,仅仅是一个动作的改变。同样的变化出现在《吃鸟的女孩》当中,可怜的鸟是真真切切被女孩吞噬殆尽,它更像道具而非单纯的意象,映衬出成长期的古怪与突变,还有父母们的苦恼与无奈。
与动物们的鲜明形象相比,埋在诸多篇目里的未知就变得极为晦涩,让人百般寻思却仍始终得不到解答。最典型的要数《荒原上》,情节上没什么难懂的,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片空白,让你始终填补不上,这种终极悬念到最后还要在黑暗中恐吓你,撕咬你。荒原上有什么?寒风劲草,寻常之地的陷阱,狩猎途中的意外收获,夫妇俩为某种仪式做了充足的准备,“增强生育能力的偏方数不胜数”,早已点出了笼罩在整个故事上的疑云,而这个偏方到底是什么,夫妇俩口中的“他们”到底是什么,夫妇俩偶遇另一对夫妇并在他们家撞见的“他”又是什么,这些答案作者早已砍去,读者也只能任由自身想象来补圆这一残缺。而像《地下》、《掘洞人》篇目中的未知,几乎在能承受范围之内,随着行文叙述的推进,未知气氛演变成了荒诞与悲伤。
在整本书当中,《以头撞地》的酣畅淋漓程度是其它篇目无法企及的。爱画画的男孩长大成为画家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所画的主题始终不变,“头在地面上撞碎的场面”,有些富人出于奇怪的目的还会特意前来订制,回头还将画作挂置客厅让宾客品头论足。画家小时候并没有受过多少欺负,最开始某位捣蛋同学抢走他的画并撕碎,谁也没料想到画家会被彻底激怒,他追上去,抓住那个足球队队长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地下砸。大家会认为这是精神失常,画家却不以为常,学生时代的两次“以头撞地”经验让他学到了如何表现更强烈的画面,而这点也成就了他的事业,隐形中拖拽着他前往并沉浸在障碍人格里的暴力美学当中。
现居柏林的萨曼塔·施维伯林是位成长中的青年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在前辈影子的基础上延伸出最独特最难以取代的个人想象,她书写日常,却擅于挖掘出隐于日常之下的荒谬、怪诞、抑郁与悲伤,美好与时光一并沦为奇异的点缀。